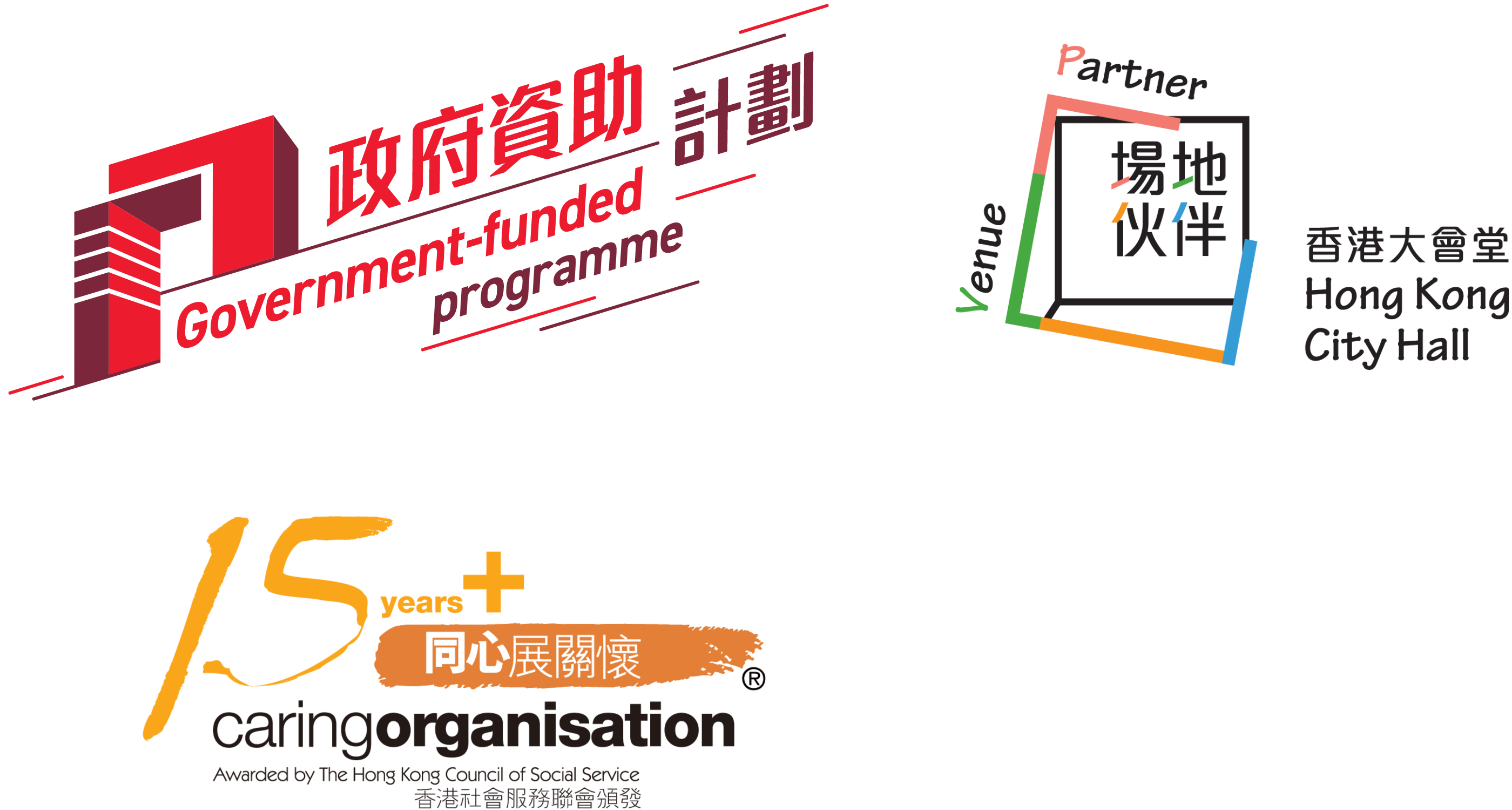戏剧文学
要过「好日子」就要等运到?
这是编剧郑国伟「暴裂家庭」系列第三部作品,由《最后晚餐》、《最后作孽》到现在的《好日子》,他的伦理剧内容都非常关心两个命题,就是金钱和血缘。个人认为《最后晚餐》要让观众感受到的是「死亡不可怕,贫穷才可怕」;而《最后作孽》就是「土豪不可怕,冷漠才可怕」;这次《好日子》则是「对抗不可怕,苟安才可怕」。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姑息养奸的乱伦故事。女主角是一位「九十后」、性格倔强的文员,她面对自己悲惨的遭遇,却选择逆来顺受,不断逃避现实,直到可以透过婚嫁走出阴霾,离开家庭。
而她以为这样可以改变命运!
须知道,伦理剧[1](Ethical play)是通过结合现实生活情况,偶尔稍带夸张的演绎手法,来讲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中具有社会关系伦理情节的戏剧。伦理剧与其他剧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主要採用通俗剧的形式,将伦理的精神体现在戏剧之中,当中包括:情感、婚姻、家庭、宗教、代沟、社会问题等范畴,这些都可以归纳在此类剧种之内。因此,伦理剧有着比其他戏剧种类更为广阔的领域,以及更模煳的边界。至于所谓通俗特点,因其主要是反映社会形态、家庭结构的联繫和相互影响,所以,主要基调是通俗,容易让普罗大众观看的剧场。剧本内容多数是描写在社会中拼搏的成年人,因为观众对于这类剧目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感,也许是剧本角色和观众的生活经歷有着相同之处,彼此较易产生共鸣。
然与社会接轨,是身为一个人最原始、甚至可以说是灵魂的原貌。剧作家就是要透过家庭伦理剧让观众窥视自己的本性和原貌。其次,就是有关情感。情感是家庭伦理剧永远扯不断的丝线,你可以和无数情人一刀两断,但是,你无法和家人彻底断绝血缘关系。这种情感犹如与生俱来的制约与誓约,同时,这种情感是激发观众想像的催化剂,让他们容易对号入座,可以不断想像角色处境并进行批判。最后,就是关于社会。虽然家庭具有个性化、私人化的特徵,但是由于每个人仍是社会中的一份子,家庭也是社会中的家庭,特别是现代家庭及家庭生活,都存在着广泛的共通性,正因如此,家庭伦理剧的敍事才能产生广泛的联想、共鸣和价值观。
家庭伦理剧当然不是宏大题材,一般仅局限于家庭敍事。但家庭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家庭是由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一个社会单元,是感情、亲情、爱情的原生地和寄生地。不管现实家庭整体状况和个体状况如何,我们对于和睦、幸福、美好家庭的欲望追求都是无止境的。因此,家庭成为文学敍事的重要领域,家庭敍事存在着巨大的创作空间。
郑国伟笔下的伦理剧,角色都充满人性的丑恶,无论是《最后晚餐》、《好日子》、《最后作孽》到《好日子》,主角都拥有一股强烈的杀气,企图杀死至亲,这种杀意是剧本的最大拉力。而这次《好日子》的杀人动机,就是来自于女儿被父亲强暴的惨痛经歷。郑国伟明白到,角色的表现形式必须以道德、性、爱或者社会家庭多样来表现出来,不同角色对于上述伦理也有不同的观点角度,例如剧中的家姐可以接受丈夫嫖妓,反而不接受丈夫光顾援交少女;妹妹可以为了每月五千元的酬金,以及婚后主人房的独立洗手间,甘愿和男同性恋者假结婚;至于母亲更加可以对于丈夫的兽性行为置若罔闻。这一切的铺设,编剧抛出了自己的角度,盼望观众可以透过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每个题目作出回应。郑国伟在这个剧本中认为,男人是最幼稚和要不得的生物;爱情已经不可信,完全失去为配偶牺牲的精神;婚姻只是为了改善生活质素;金钱的价值凌越亲情,永远是「亲生仔不如近身钱」;以及我们永远要面对邪淫的本性。
当然,以上的题材和观点在戏剧中可谓屡见不鲜。有趣的是,其实这个剧本可以给予观众另一个思考层面,甚至超出了故事表面的想像。近年韩国电视剧在香港大行其道,伦理剧亦是其重要剧种。韩国的伦理剧,注入了独特的人文情怀、契合韩国悠久的传统儒家文化,亦老少咸宜。当下,风格多元的韩国伦理戏剧,已经成为韩国创意产业格局中颇具市场竞争力的类别。在以「家」为中心的故事框架中,韩剧典型地呈现出「回归传统」和「颠覆传统」的伦理文化观念。李淑妍编写的《通往机场的路》就是最成功的范例。此外,在儒家文化「家国同构」的思想下,韩剧在某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和社会意涵。
那么,郑国伟的《好日子》有这种意识投射吗?我认为是有的。假设女主角的「家」代表香港,观众现在正好看到三代人面对同一个重要问题,表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首先,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父权象徵显然,他既是当权者,也是施暴者。面对不能撼动的地位和势力,现在年过半百的母亲採取姑息态度,也许因为这个男人是自己拣选,正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己知」,主观意愿还是希望「致力建立和谐共融的社会」。至于首名受害者家姐,她的生存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女儿彤彤的未来着想,为她寻找一个「安全环境」,在一个没有被「男人」威胁的情况下快乐地成长,自己身为母亲的个人感受已经不再重要。女主角则代表着年轻的「九十后」,她只会选择逃避,选择义无反顾地离开不安的地方,完全没有计划要改变成长环境。所以,宣传单张也强调她的个人信念─
「如果他能带我逃离一切,我愿意。」结论是,没有任何人对这个家有归属感。
要成功投射出这个层面的想像,导演方俊杰的艺术选择最为关键。他较早前为演艺学院执导的小剧场作品Lysistrata,透过出色的导演手法,成功为古希腊喜剧作家亚里斯多芬(Aristophanes)于西元前411年发表的这部作品,重新注入当代戏剧元素和舞台美学设计,给予剧本新生命,令这齣被喻为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并以反战为题材的荒诞喜剧,蜕变成为一部属于香港社会的政治寓言剧。当然,方俊杰这次可能选择不去呈现《好日子》故事中赋予的社会政治层面;若然如此,观众就要聚焦在整体的演出节奏上,因为剧本中的吵闹场面比较多,导演就如指挥家一样,如果在吵闹节奏上没有适当处理,演出可能会沦落为「得个嘈字」!但是,我仍然对方俊杰满有信心。
最后,关于故事结局方面,编剧的描写是有心思的,因为对于剧中角色而言,现在的结局毫无疑问是一齣喜剧。但是,从观众的角度而言,这是一齣悲剧。这种描写方法,有点像「荒诞派」的戏剧作品,多数荒诞派戏剧的模式是悲喜剧。尤其是剧中父亲的结局,竟然和一瓶「唔知咩酒窖生产嘅大陆名酒」扯上关系。这个结尾令我联想到贝克特(Samuel Beckett)在《终局》(End-game)中所说:「没有甚么比不幸更有趣;这是世界上最有喜感的事情。」到底哭笑过后,我们可以汲取教训吗?还是如黑格尔(G.W.F. Hegel)所言:「人类从歷史里学到一个教训,就是没有学到任何教训!」
(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1]参见百度百科「伦理剧」条目:https://baike.baidu.com/item/伦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