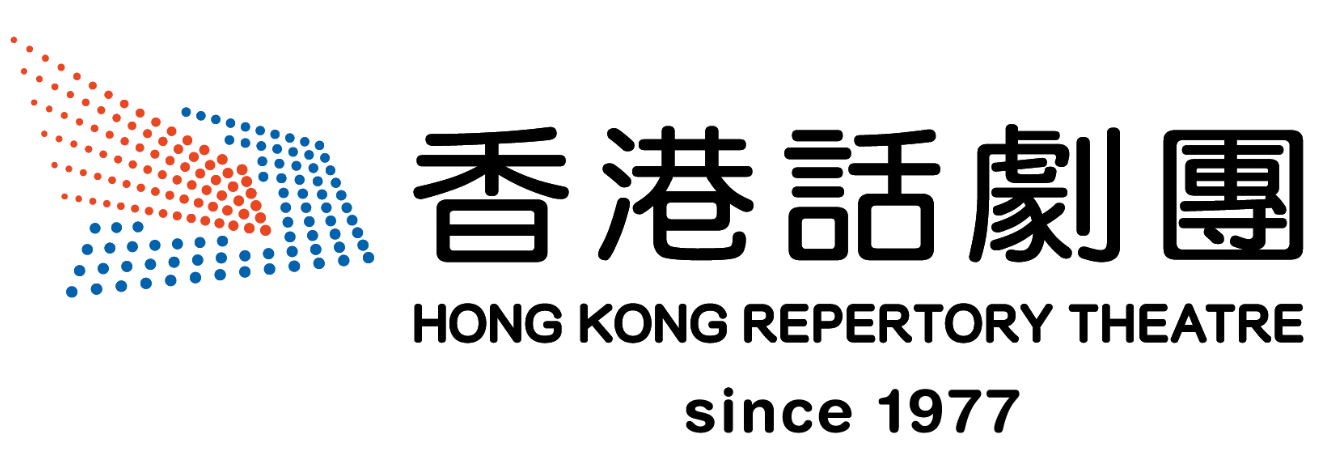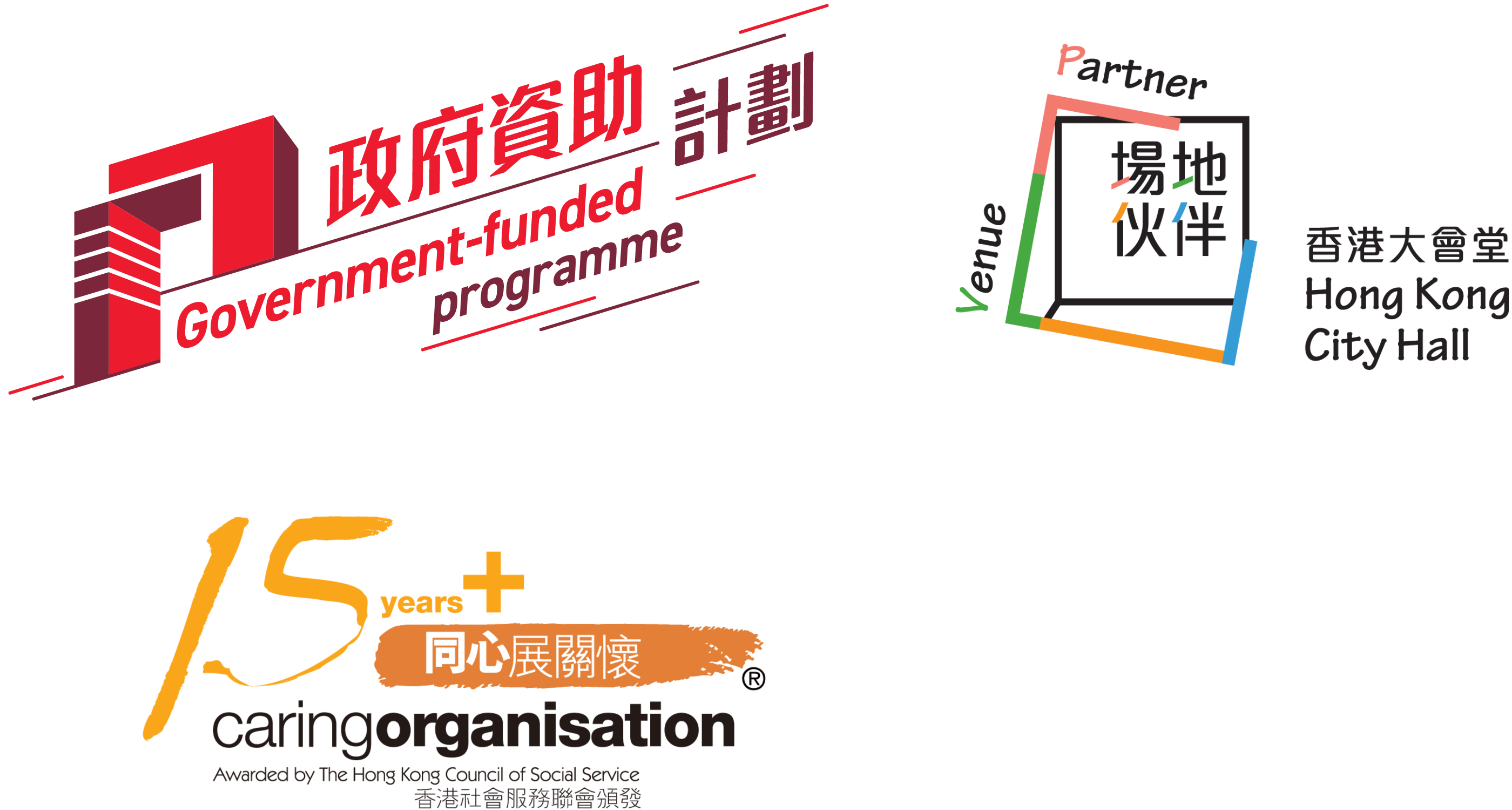戏剧文学
时间的幻象─《盛宴》赏析
我读中学时十分流行日本漫画《男儿当入樽》(スラムダンク),这齣漫画,后来更制作了电视动画版。还记得当时跟友人笑说,明明实际球赛入樽祇花短短几十秒,动画则把这数十秒拉长至三十分钟或更长,迟迟不知谁胜谁负,吊着大家的胃口,好增加收视率。如此情况在剧场里更是常态─ 演员跟观众共同分享了九十分钟的实时演出,但作品为观众制造出来的时间假象,可以长达十年以至二十年,也可以祇短至五分钟。「时间」,无可否认是戏剧及剧场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不论剧作家、导演、演员甚至设计师均要处理及面对它。如何把时间拉长缩短,成功制造「幻象」,就要靠各种剧场手法去调节观众的感知。《盛宴》(The Big Meal)把弄时间的方法,则由作品的结构入手。
《盛宴》剧本表明,需要四对不同年纪的男女,齐集老中青幼,共八位演员演出。故事以Nicole及Sam这对夫妇的一生为主轴,每场戏都发生在大家最熟悉不过的场景─餐厅。虽然围绕二人,却又非由同一对演员演绎。故事开始时,由年轻的一对演员演绎Nicole及Sam,讲述他们在餐厅相识,随即堕入爱河。但当故事发展到Nicole及Sam结婚,并为人父母时,就会交由中年的演员演绎,而年老一对演员担当其父母,年轻一对演员则成为Nicole及Sam的子女。如此类推,最后由年老的演员,演绎Nicole及Sam为人祖父母的阶段,中年及年轻演员变成二人的子女及儿孙。故此,为了方便表达演员轮流演绎不同角色,剧本的排版跟平常不同,除以横向排版外,更以数字(女一、男一、女二、男二等)代替角色名字,指示演员要担当的角色及其对白。
| 女一Alice | 男一Robert | 女二 Nicole | 男二 Sam | 女童Maddie | 男童Robbie |
| (沉默) | (沉默) | (沉默) | (沉默) | (沉默) | (沉默) |
| 我想出去睇玩具。 | |||||
| 都未叫嘢。 | 我又去。 | 我想自己去! | |||
| 你唔可以再买玩具嘎嘞。 | |||||
| 我又去。 | 就喺商场之嘛。 我净系睇吓咋。睇吓有没新玩具。 |
||||
| 我又去。 | 唔制,我要自己去。 | ||||
| 净系睇吓就得。 | 我又去。 | 唓,成日都要就佢。 | |||
| 同埋Maddie去就可以去。 | |||||
| 好啦,行啦! | |||||
| 咩呀? | |||||
| 你到底想唔想去先? | 条件就系恁样。 | ||||
| 畀佢快尐去快尐返啰。 | |||||
| 喂Robbie! |
《盛宴》的剧本选段(陈敢权翻译)
九十分钟的剧本涵盖一个家族五代人,可以想像到,当中有许多情节被删除。而五代人的故事,单单角色也有廿六位之多;演员经常换角,剧作者选取了在餐厅进餐的场景作为恆常的切入点,正好为繁杂的情节带来一点平衡。《盛宴》里的时间幻象既浓缩又精简,但正因由多位不同年纪的演员轮流饰演同一角色,演出节奏的转变就相当明显,感觉有如加速:上一场明明年轻的Nicole及Sam说不要结婚不要小孩,下一场他们不用变妆就已经「变老」,带着小孩了。LeFranc在访问里说过,他身边许多朋友本来从不打算结婚生子,但到了某个年纪,又会突然改变其前半生所相信的人生观,投入为人父母的行列,他正想捕捉这种改变的速度。这种处理的另一原因,也是我心中更为明显的解读,正是老生常谈的「有其父必有其子」现象。
《盛宴》所折射的,正是每个家庭都可能经歷的场面。子女是父母的延伸,就算我们多么的不情愿,为人子女总会带着父母的影子生活。主角Sam也一样,他年轻时也讨厌自己的父亲,更抗拒成为父亲那样一个口不择言,不甘被家庭成员所冷落的人。但当Sam年纪愈大,到了为人老父的年纪,竟然跟他自己的父亲一样口不择言,惹子女讨厌,有些说话甚至跟父亲何其相似。正正因为由同一位演员先演绎Sam的父亲,再演绎已为人父的Sam,加深了观众对两者为一的印象。LeFranc有效地描绘了「家庭基因」的承传:「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祖父当年在我母亲十六岁时所讲过的一番说话,怎样影响着我及我的妹妹?我一直对这些关系的连结很感兴趣,特别是这些累积起来的时刻。我没可能完全了解她年轻时所听所闻,但我深信她当时的经歷决定了她怎样对待我,从而影响着我
的人生。」[1]
剧本虽然横跨几代人,但读来并未有强烈的时代变迁之感;取而代之是一种「无尽的当下」的感觉。剧作家甚至故意删减任何让人联想到年代的指涉,例如人名或物件名称等;可以说,《盛宴》里祇有当下,缺乏过去与未来。时间经常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互不重叠,过去了的已不存在,将会来的未曾存在。但若过去与未来都不存在的话,古罗马时期的神学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0就提出,从逻辑而言,时间理应不存在!对奥古斯丁而言,时间不应被描述为存在之物,反而由主体的经验去思考时间为何。所谓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其实是主体对三个时间点的思考,而思考都祇能由现在的视点出发:「在心灵之中我们找到三种他处所无的时间:思考着过去的现在是记忆,思考着现在的现在是对当下的察醒,思考着将来的现在是期望。」[2]存在的其实是我们的记忆、察醒及期望。过去了的歷史并没有真正消逝,回忆影响着当下的你和我;对未来的期望,左右我们在当下的决定。时间一直是哲学里一道难解的题,我并非哲学专家,不敢班门弄斧,但这种以经验诠释时间的观点,正好回应到我LeFranc这剧本时,这「无尽的当下」之感。
每种剧场手法均有其优点缺点,为了突显「时间」这主题,LeFranc或许牺牲了剧情的复杂性,将两位主角的人生直接而顺序地写出。当中发生的事件,譬如生育、结婚、家庭争执及外遇等虽能引起共鸣,但涵盖范围宽阔,有些桥段可能着墨不够。《盛宴》首演于2011年,在美国公演后也有评论指出,这种转换形式致使观众未能投入到两位主角的心理状态中。另外,这个作品对导演的难处,就是在不断换角下,依然能让观众能分清谁是谁,并掌握故事的发展。为了清楚表示角色的转变,剧作家在剧情铺排上增加了角色进出舞台的机会,让演员不时因应需要换戏服或转妆。台位及舞台调度都要清爽明快,因有部分场次短至祇有几句,就已转换了时间甚至角色。加上《盛宴》一景到底,导演在整体节奏掌握方面更要拿捏得宜,如借助灯光及音乐去制造气氛及节奏的转变,免得被剧本的形式牵着走,甚考导演功夫。但说到底,都要演员能掌握各个角色的外型、声线及性格特点,特别是Nicole及Sam两位主角,共由六位演员演绎,角色的一致性尤其重要。除了《盛宴》,以时间为题的戏剧作品,其实为数不少。LeFranc自己就承认,受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漫长的圣诞晚餐》(The Long Christmas Dinner)启发而写成《盛宴》。《漫长的圣诞晚餐》野心更加大,每场戏均是同一家庭的圣诞聚餐,但短短三十分钟独幕剧竟跨越了九十年的时间。这个写于1931年的剧本,虽然没有怀尔德的另一剧本《小城风光》(Our Town)有名,也很值得各位一读。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的「时间作品」系列亦是以时间为题,较为人熟悉的想必是《玻璃侦探》(An Inspector Calls)。剧本的情节均根据一个时间的理论建构出来,剧中角色因活在非一般的时间及空间,令生命有所转变。戏剧以外的剧场作品,要数威尔森(Robert Wilson)的一系列作品,例如歌剧《沙滩上的爱恩斯坦》(Einstein on theBeach),则故意拒绝玩弄剧场里时间的幻象;剧长四个半小时,不断藉重覆的画面提示观众共同经歷着的实际时间。
《盛宴》的故事未必最突出,但剧作家由结构入手把弄时间幻象,着实创新。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有曰:「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如梦般的《盛宴》,Nicole及Sam浓缩了的人生,所剩下的还有甚么?
[1] Madden, Jennifer. A Peek into the Creative Process:A Conversation with Dan Lefranc, Author of The Big Meal. Gamm Theatre: docs.wixstatic.com/ugd/bd75c5_3257479f7e294a23b1017cc4b3f86223.pdf.
[2] 郭世恒,〈奥古斯丁与时间问题〉,01哲学:philosophy.hk01.com/channel/概念/97578/奥古斯丁与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