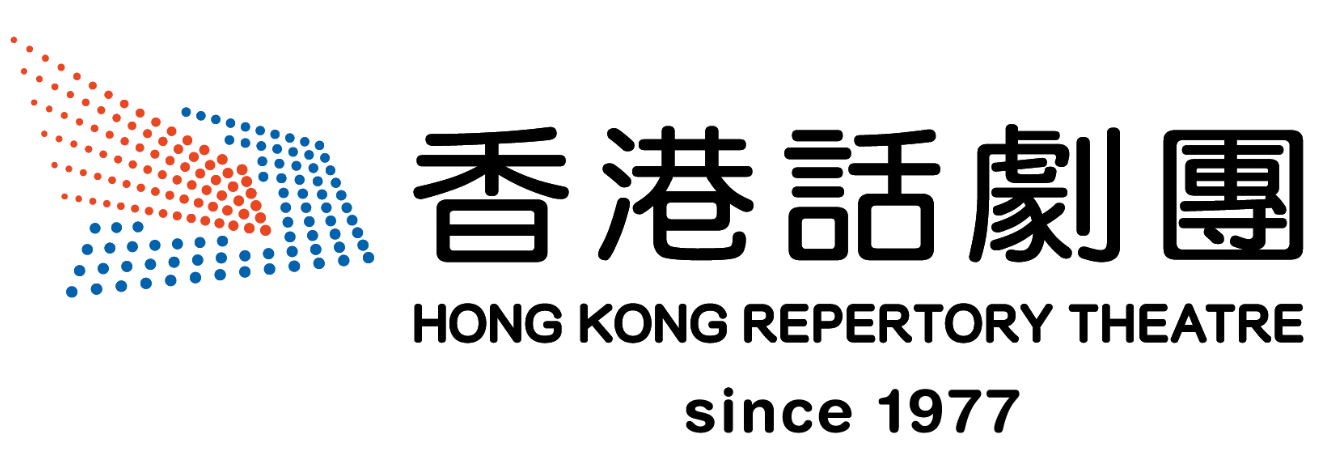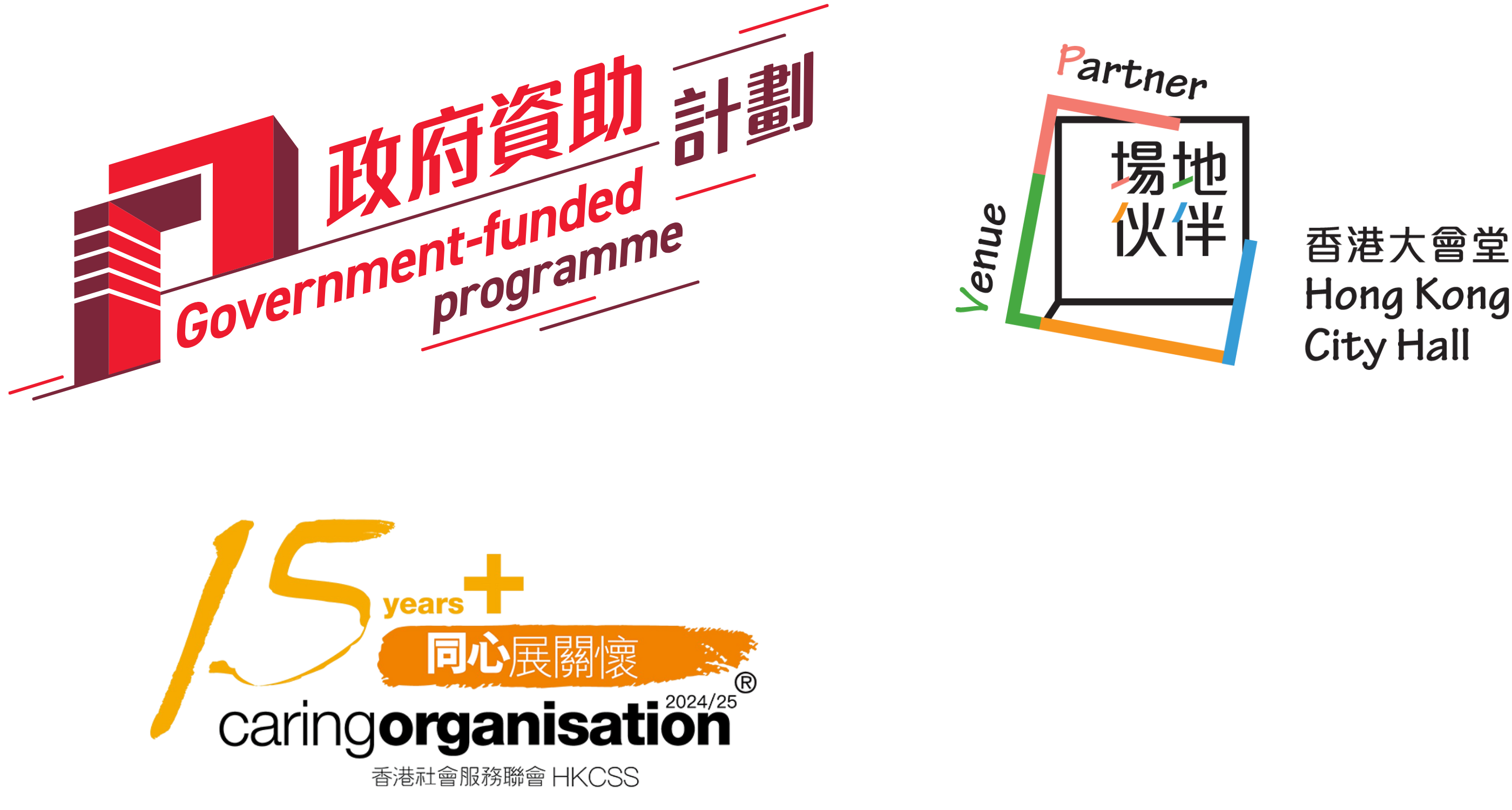戏剧文学
《骄傲》:骄傲者的折腾
「骄傲」,或说「傲慢」,在基督教传统中是着名的七宗罪之一,原意跟人性的恶念无关,而是指魔鬼撒旦滥用自己的权力,试图挑战上帝。在更古老的古希腊文化里,「傲慢」通常是指拥有社会地位的人高估自己的能力,继而变得脱离现实,甚至做出挑战神明的行为。两种说法语境迥异,但道理相通,在西方文化传统里,傲慢心理皆被贬为罪愆,甚至有渎神之意,故常被视为最原始也最严重的罪行。
但自尼采(Niet zsche)之后,谦卑不再一定是美德,傲慢也可以是酒神[1]意志的伸张。在王昊然的剧作《骄傲》里,他便将傲慢─或用回「骄傲」这个语气较轻的词语─设置在廿一世纪的香港里,也不再以审判态度看待。廿一世纪没有神,香港也不是西方,如果有一种可以被称为「骄傲」的当代人特质,那肯定不是遇神杀神的冲劲,而是反社会反世俗的身份自觉。《骄傲》里的主角Jason是一名来港生活差不多七年的深圳人,他的广东话没有口音,外表和生活习惯跟一般香港人无异,但在一些小骨节眼上,偶然会被人发现他原来「不是香港人」,这些漏洞便成了刺痛他自傲心态的利刀。而更大问题则是他有一颗想当香港人又看不起香港人的心,于是表现起来,他骄傲自大,但在内心深处,却有一片面积不少的自卑阴影。
我们很容易便会落入「中港文化矛盾」这类套路去解读《骄傲》这部作品,但编剧王昊然似乎更乐于着墨在像Jason这种自傲与自卑并存的矛盾内心,远于多浮泛的社会文化矛盾。剧中对Jason的刻划,有点像卡缪(Camus)笔下小说《异乡人》(L’Étranger)里的主角莫梭(Meursault),虽然《骄傲》不是存在主义式作品,Jason也没莫梭那种形而上的虚无,但剧中所弥漫的局外感,同样浓烈。Jason的表现远比存在主义者入世,骨子里却一直迴避着现世生活,尤其在他与Tanya之间若即若离的爱情关系上。由此看来,虽然《骄傲》剧情简单,故事框架也不大,但王昊然颇具野心地要处理一个难度不小的人性问题:当现实世界也矛盾重重时,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如何在「保持高贵的精神」和「返回世俗生活的安稳」之间作出抉择。
全剧故事聚焦于Jason跟Tanya的爱情故事上。Jason对Tanya抱有好感,却一直跟她保持距离,当中有自骄自傲的心态,亦因过去的情伤而不愿打开心锁。而Tanya则一路主动进击,处处围捕,Jason却总在口头上摆出高傲姿态。这段情感攻防战建基于一个人的骄傲之上,在戏剧典故上有一齣着名作品可作唿应─ 莎士比亚的喜剧《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驯悍记》剧名中的“shrew ”是指「泼妇」,用广东话俗语可以译作「老虎乸」。剧中女主角凯瑟丽娜(Katherina)桀傲强悍,既自负又看不起男人,但在一连串爱情攻防战之后,她却被驯服下来,心甘情愿地下嫁一个原本只为鉅额嫁妆而来的外地人。最后凯瑟丽娜甚至声称,自己昔日的高傲并不可取,妻子始终是要听从丈夫的话。
在《骄傲》里,Jason就曾经以《驯悍记》一剧为喻,指爱情是一个驯服和被驯服的过程,更因此质疑真正的爱情其实并不存在。我们大可以把他这番「伟论」解读为一种心理防卫机制:他不相信的并不是爱情,而是爱情中的自己。他骄傲自大,不愿在他人面前妥协,原因很可能是他的自卑心作祟,他深怕如果偶一不慎,在爱情路上跌上一跤,就会失去一切,所以他才要摆出轻蔑爱情的姿态,以保护自己。《驯悍记》的闹剧结局常为后人诟病,指泼妇女主角的逆转太过理所当然,也太过自贬身价。而Jason所恐惧的,恰恰就是这个庸俗的结局会发生在他身上。
除了Jason和Tanya一对,剧中还有Ryan 和Cindy一对。Ryan从美国回流香港,对香港文化不甚了解,因不懂得唱【狮子山下】而遭人耻笑,可他却是个年赚百萬的打工皇帝,职场上的成功令他把香港视作一个英雄地,更把「佔中」时的催泪弹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血性」[2]。但他在来自内地的空姐女友Cindy面前,又如观音兵一样千依百顺,偏偏Cindy却暗地里有外遇了。这段关系,俨然是Jason批判《驯悍记》的有力佐证:在爱情里,家境优厚的Ryan因被驯服而失去自我,换来却是被对方背叛。可是,编剧王昊然饶为巧妙地将Ryan设定为Jason骄傲心理的反面:Ryan道破Jason心理弱点,催促他摆脱心理障碍,接受Tanya的爱;他更在全剧后半段妥善处理了自己跟Cindy的关系,最后喜剧收场。反而Jason却超越不了自身,而招致一个相当可怕的结局。
《骄傲》不是喜闹剧,更不是悲剧,王昊然似乎更希望让戏剧性在反覆角力的对话中扩散,对人物内心矛盾作更多刻划,而不是经营一个架构严密的故事。因此在篇幅不长的剧本里,几个角色在爱情关系上几度反覆,角色的心理折腾也愈见立体。关于「傲慢如何毁掉爱情」这个母题,文学上另有一经典文本可作对照:小说《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作者珍‧奥斯汀(Jane Austen)匠心独运之处,是她没有犯上莎士比亚、凯瑟丽娜和Jason的错误,把爱情跟傲慢的关系想得太简单了。反而借现代长篇小说的格局,奥斯汀深刻地表现出一群置身爱情之中的角色,怎样各自面对自身的傲慢。傲慢是性格使然,也是社会身份的枷锁,在《傲慢与偏见》里,不论是社会地位、财富还是文化修养,全都是令一众角色变得「傲慢」的素材。他们亦因着各式各样的傲慢,几乎失去了跟他人相知相亲的机缘。
《骄傲》的故事坐落在今天的香港,文化身份认同(cultural identity)还是无法绕过的议题。剧中稍有提及「佔中」,然而更能精准地表现剧中的「文化母题」的,却是一个饶有科幻意味的设定:一个登月的中国太空人的幻想场景,穿插于两对男女主角的写实场景之间。观众最终会知道这个太空人到底是谁,但自一开场起,这个登月太空人即代表了比儿女私情宏大得多的国族身份问题:中国登月,大国崛起,身为中华儿女终可骄傲地起来了。然而面对「香港」这个中国国族身份的爆破点,王昊然保持着其一贯关怀,即着眼于一个「新香港人」的流徙意识:要离开内地的老家来到香港,当一个堂堂正正的「香港人」,却又为着骄矜的文化自觉,不甘于为了承迎现实而要把自己「变成香港人」。这就正如一个逃逸于地球引力以外的太空人,既自傲于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却又为冷冽寂静的外太空而心怀孤绝。可是,偏偏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总不能这样自骄自绝,而是要在浮浮沉沉的世俗生活里营营役役。
剧作主要由Jason和Tanya,以及Ryan和Cindy两对男女的关系贯穿,而Jason跟Ryan、跟Tanya和Cindy亦各自份属室友,于是这两男两女组成的通俗爱情剧格局,便成了上述的「现实世界」和「世俗生活」,与「登月太空人」这个隐喻着「精神贵族之心」的意象形成强烈对比。而在当代世界里,骄傲不再是罪,而是一种病弱心理,尽管剧中充满粗鄙刻薄之言和政治不正确的人生态度,但戏剧从来不是用作道德批判的。只有复杂的人性,才是戏剧的不败主题。
[1] 作者註:尼采以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戴奥尼索(Dionysus)为古希腊两大艺术力量,太阳神象徵诗歌、预言和光明,酒神则代表戏剧、生命力和狂喜。尼采认为,古希腊悲剧衰落正是原于「酒神精神」渐渐被「太阳神精神」所取代,「酒神精神」亦代表尼采对西方文明里的悲观主义的批判和拯救,也唿应了他的「超人意志」学说。
[2] 编按:就2014年9月展开的「佔领中环」行动,香港警方于9月28日黄昏至29日凌晨,向示威者施放催泪弹。详见维基百科「佔领中环」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