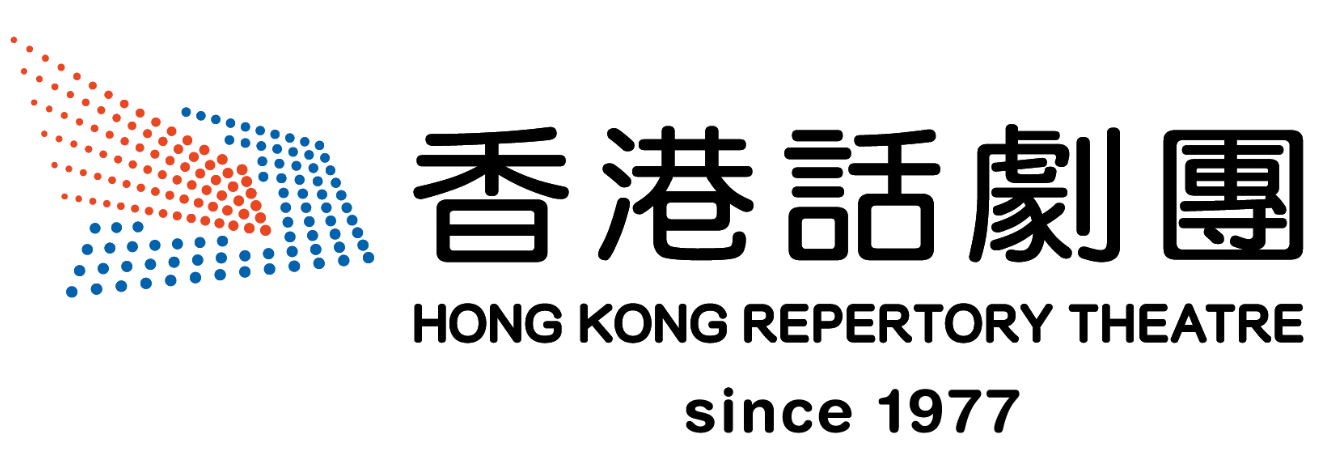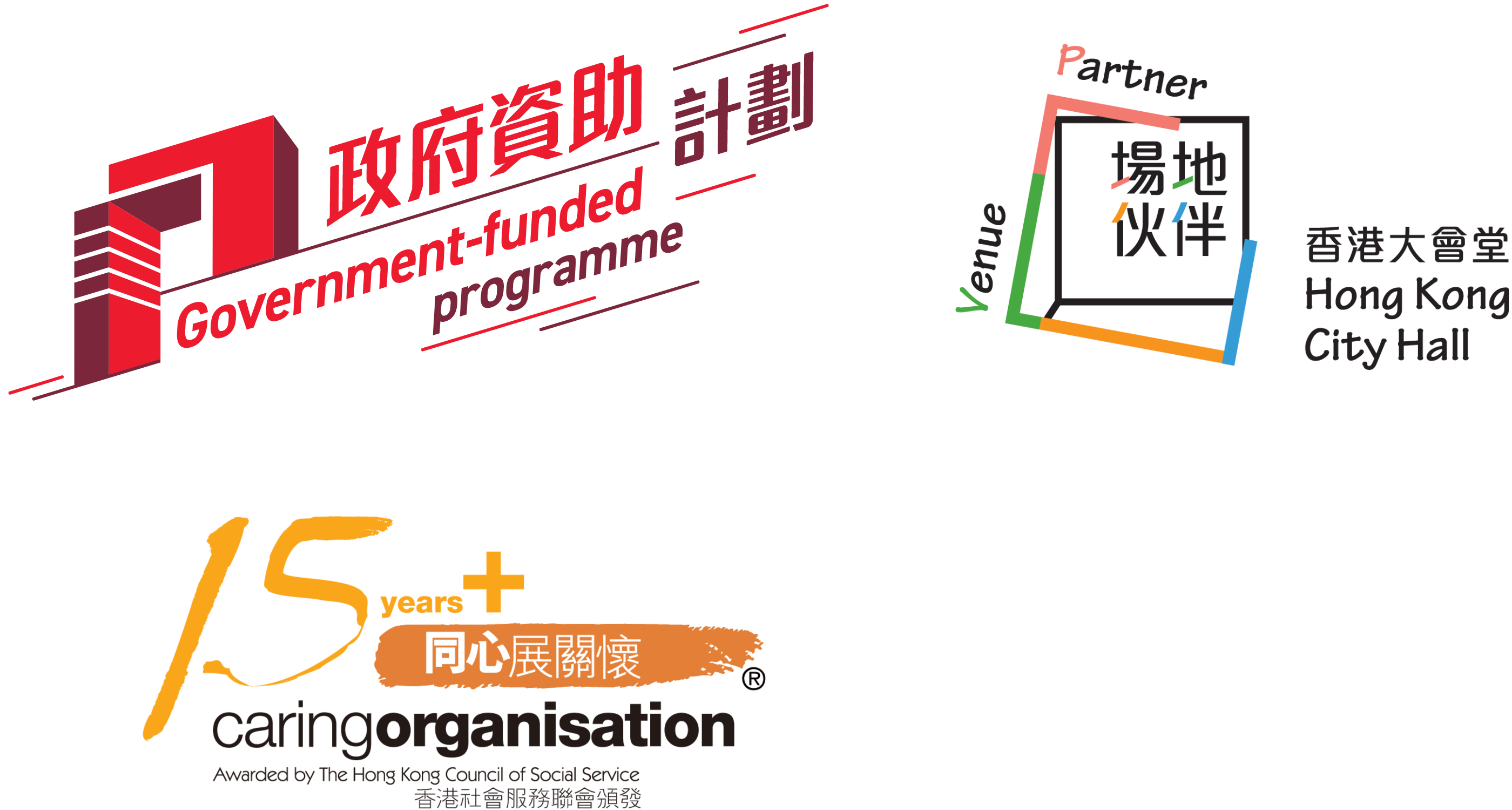戏剧文学
梦里梦外 ─《如梦之梦》导赏
仪式与故事
进入剧场,你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来。不久戏开始 了,观众就给演员包围着,他们顺时针绕圈。绕圈, 从 此在剧场内不间断地进行。这个往前行进的动 作,一开始便是个集体行为。或快或慢,连续不断,带着东西的,不带着甚么的,明显地带着某些情绪 的,看来似乎比较漠然而无所谓的⋯⋯慢慢地这个 绕圈已经不单是一个剧场内的「行为」了,它是个有 意为之的剧场符号,它是一个仪式。然后,你会发觉,这个戏的仪式可多呢!「点蜡烛」 就是一个。医生想听五号病人的故事,病人要她带 支蜡烛来。先要点起蜡烛,故事才可以开始。唯有 仪式,才显出故事的庄重性。你购票看这个戏,要 经过到票房排队、付钱,到时候要预算时间换衣服 出门赶交通步过一段路程等等程序,你若把这些视 为「仪式」,这个戏也许会更显分量。「仪式」通常 有它的传承关系。「点蜡烛」就贯彻首尾,到第二部 分顾香兰讲故事。蜡烛、古董烛台⋯⋯你恍然大悟:五号病人的做法应该是从顾香兰处来;顾香兰呢,也自有她建立这个仪式的来处⋯⋯
于是,光是从仪式着眼,你也看到趣味,看到美。
「埋东西」也是仪式。今天我们叫「时间囊」的埋 东西,在戏中也一再出现。是情节,也是仪式。这仪 式在戏里由江红开始,她在土地以至地板埋下这个 或那个东西,给未来某个时间的某个人发掘出来, 从而发现出特别的意义。这,也是一个,让人珍重的,仪式。
扩而大之,生活上的起居日用也可以赋予「仪式」的意义和分量。我们从外面回到家会脱外衣,从家里外出会穿衣。但是,假如本来要穿上的外衣给人拿走呢?又假如远行时要脱去外衣,让身体变得干干净净呢?那都代表甚么意思?
当然最重要的仪式还是环形剧场的佈局,和与之配合的持续绕圈而行。它有宗教意味,在印度以至西藏,信众顺时针绕行敲钟礼敬;在一般中国寺庙,拜谒主尊之后,我们会顺时针瞻 敬侧面和背后的菩萨。绕行也有哲学意味。这唿应着东方的时间观 念,春夏秋冬,生长收藏。萬物復苏,生生不息。绕行让一切回到原点。戏里自然有直线元素,例如火车,尤其是在第二部分顾香兰的故事里。是近代的 火车改变了时间观念,因天时而各处不同的时间, 却因着火车而必须准确与归一。而直线而行、通往未知的时间,也似乎根本改变了人的命运,包括顾香兰的命运。但是,直线到底只是局部,包围着直线的是个更大的圆。就如任何朝前飞驰的火车都离不开地球,最后,都回到原点。
谛听死亡
回到原点的,本来就是生命。对很多人来说,生命在医院开始,最后,也在医院结束。
这齣戏是在医院开始的。戏的第一个说故事者是医生── 一位刚毕业、马上要投入理想专业的医生。可是 她没有足够心理 准备,迎接她的是死亡、死亡、死亡、死亡。第一天上班,她当值的病房便连续死了四个病人。
我们「旁观他人的痛苦」,应该怎么办?这是个当代众所关心的问题。这个戏的年轻医生首先是困惑、 无助、沮丧、挫败,然后,她愿意努力去学习帮助濒临死亡的病人。「自他交换」也好,「听他说故事」也好,其实都是要接近以至进入濒死者的生命。
拒绝旁观,谛听死亡。这是推动整个戏进行的力量。
点起蜡烛,它的光划出了说与听的空间。荧荧晃动的那一点烛火,恍似微弱然而真实的生命。这小小的一点烛火,本就是「主」字的第一笔。宗教与政治都取这个字去称唿最有力者。面对烛火,我们会庄严地思考生命是甚么,我们会卸去装饰,拨去冗余,珍惜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再没有任何时候让人更懂得「主」和「从」的关系了,回归本源,就一如 《庄子‧养生主》中这「主」字的意思。这时,述说故事者认真地整理他的生命,谛听故事者仔细感受别人的生命。这个从死亡而来的新的关系里,有智慧,有美。
《 庄子‧养生主 》篇以「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结束,强调薪传不尽的关系。或许正可以和这个戏相唿应。我们在演出过程会遇上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有预计中的,也有猝然而来的交通失事、高处堕下或心脏病发,不一而足。而最集中表现死亡的无可预计,是五号病人在说他故事前的「外一章」:西藏游牧夫妻的故事。新婚的牧羊人在幸福的状态下无端地失去爱妻,却在陌生地方得到个刚失去丈夫的女人做妻子,然后又在最幸福的情况下突然失去一切。但原来这都只是一场梦。兜兜转转,甚么得与失都不过是虚幻,牧羊人穿过死亡回到原点。似乎真实不过的生生死死,到底只是个梦。
余光中说:「一盏灯,推得开几尺的浑沌?」(《守夜人》) 剧场里的荧荧烛火,会给我们光照出几多生命的执着与愚蒙?
梦与真实
我们都有梦的经验。我们有时会想:今天晚上或许也会发个梦吧?但是,我们不可能预计这或会发的是个怎样的梦。观众进场之前,都知道将会看到一个关于「梦」的故事。戏就叫《如梦之梦》。不是「如梦」之人生之风景之境界。第二个「梦」字强调这「梦」不是喻体而根本就是本体。说「如梦人生 」还认定有个「人 生」在,而赖声川说:「如梦的终究还是个梦,只是你不晓得它是『梦』罢了。」
都只是个梦,梦始终会醒。绕圆而行的都会回到原点。我们大概都会预计,一如那位西藏牧羊人的妻子,戏里面的失踨者死亡者,最后,或许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回来。不是有人这样说吗:人死之前,一生种种都会以最快的速度闪回来。
失踪的回来了。埋下的给发掘出来。五号病人的妻子、江红、王德宝、伯爵。又或者,这些人只是以另一个身分,出现在另一个人的另一形态面前?
或许都是另一形态。正如折磨、痛苦,换过另一形态,它或者竟是 快乐、璀璨呢?同样的,快乐、璀璨,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是折磨、痛苦。江红在戏 里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甚么我们最爱的东西给我们最大的快乐,也给我们最大的痛苦?」这问题不容易答。我们只能安静下来,用心去整理,去谛听,我们或许会有新发现。
梦中的痛苦不会是真实的痛苦。
经验
看这个戏当然是难得的剧场经验。观众要一直转动自己的椅子,去寻找要看的东西,看这个复杂而简单的故事。这个戏真复杂。故事中有故事。梦中有梦。一层又一层的,好像俄罗斯套娃,也好像易卜生晚年的《培尔金特》(Peer Gynt),戏中主角坐下来剥洋葱,一层又一层的剥下来,直至最后。
不过,这个戏其实也挺简单。生老病死、爱情波澜、避难海外长期流放,以至妓女遇上过分投入的男人⋯⋯独特框架里的故事其实都不新鲜,而且,说故事者如五号病人、妻子和顾香兰等,在说自己故事之先,都来一个「外一章」,并与一开首集体说的庄如梦故事相应,都是一把一把开启这个戏的钥匙呢!
藉着种种仪式构成的框架,我们可以用七个多小时,耐心地跨越情节,自然而然地、不自觉地以正常的唿吸进入他人的故事,去经验他人的生命。这也算是「自他交换」的一种方式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经验使「自己」成为「他人」。
这是《如梦之梦》在香港的第二次演出。它重临旧地去寻找新的生命,就像一次旅行。戏、人生,以至梦,都是一回不确定的旅行。江红离开中国之后不知道以后会怎样,顾香兰决定到法国也不敢设想未来,发着烧出发的五号病人当然也一样。生命本来如此。人生一直在正常轨道上走的医生,因为第一天上班马上碰到四个病人死亡而感到挫败,这才始了探问,才开展了这一个叩问生命的旅程。
旅行不是旅游,你没有得到甚么「丧拼」战利品,你只是获得独特的旅人经验。同样的,你这次不是「看了」一齣剧场经典,甚至不是「看了」一齣戏。你是「经验了」一次独特的剧场之旅,它关于心灵,关于你自己。
谁是这个戏的真正主角?谁最后能够「看见自己」?江红?顾香兰?五号病人?医生?或许是,或许都不是。这是个颠覆 剧场习惯的演出,佔据中央场 (centre stage) 的,是作为观众的你。
张秉权
戏剧艺术、艺术评论与艺术教育工作者、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