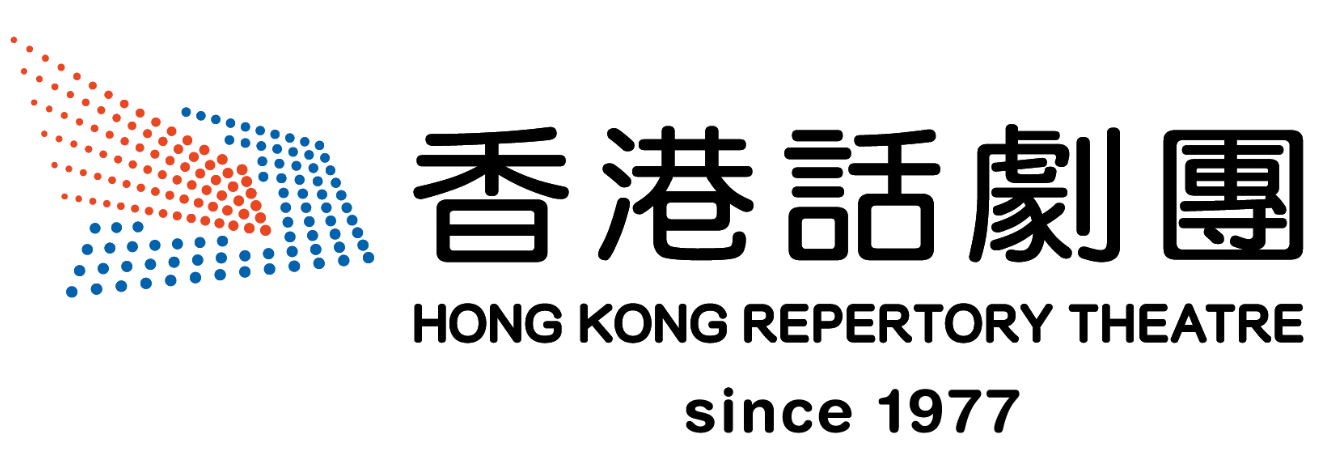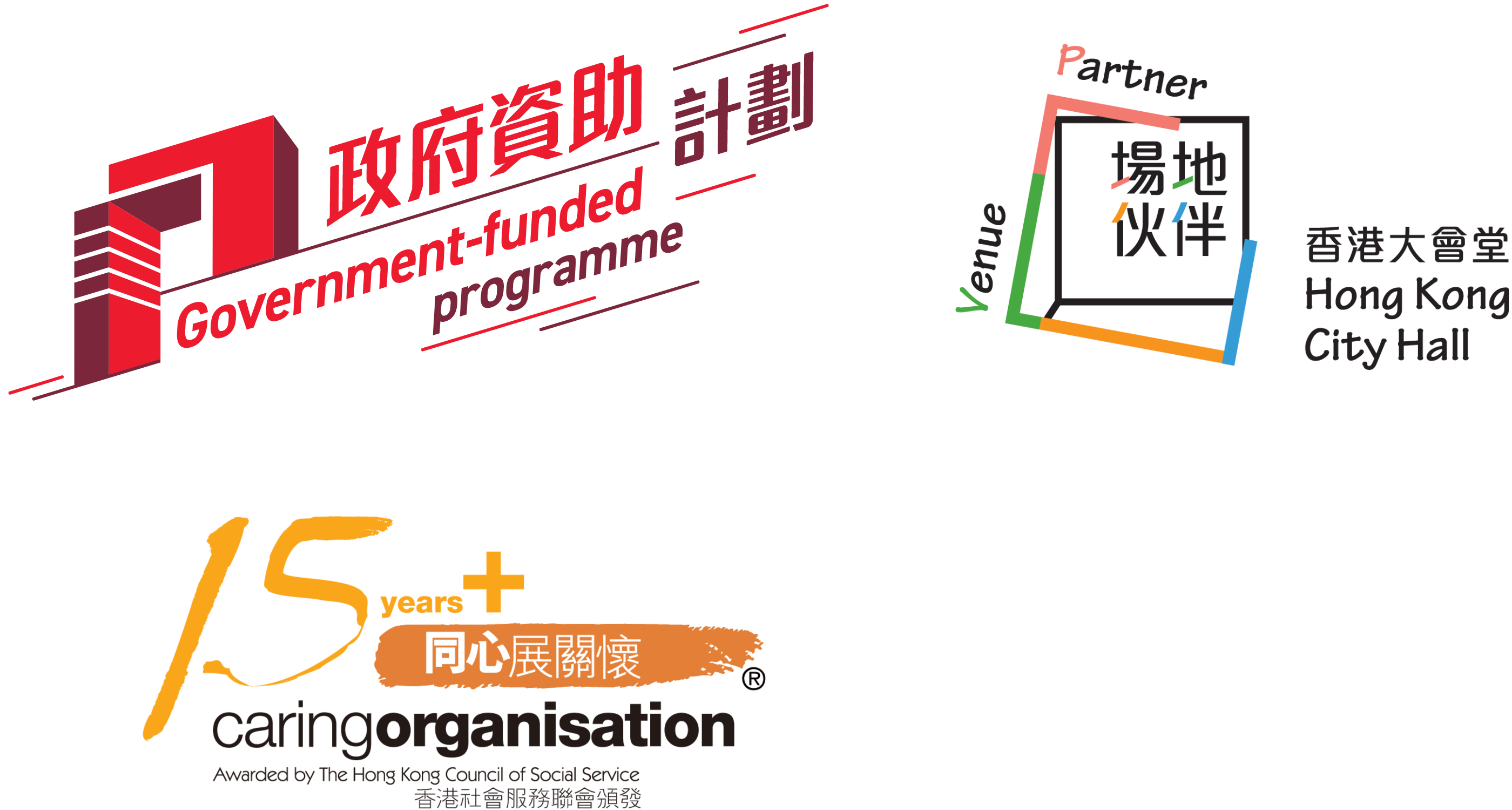戏剧文学
《叛侣》:对话,无止境的隔阂
对话失效産生撕裂
在对话失效的时势看《叛侣》,我特别关注到当中的语言失效,人与人之间变得废话连篇,没有一句是为了与对方沟通而发的吊诡。说话没有起任何作用,情侣如是,香港如是,社会现实如是。背景不重要,结局不重要,是谁扮演谁不重要。自杀是幌子,失踪也不是重点,爱情倒真的变得无色无味无形无效。而关系呢?正中要害的,是与人同在时仍然隐隐约约的那份疏离感,愈接近却愈远离真相,愈有陌生感;愈渴求亲密,愈崩离割裂。
爱是甚么?这千萬年以来人类皆未能回答的提问,这齣舞台剧呈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无爱偏要恋」的状态,任何关系没有保证、没有延伸、没有盼望,会是怎样?一只鞋、三部分的戏、五对情人,本来没有多大关联的,像蝴蝶效应,一旦对话发生了,就被 牵扯入莫名的沟通艰难的漩涡里。一只高跟鞋,一只靴;一封信,一通电话 ─ 前者象徵行走、离开,后者象徵沟通、连接。事不关己,却不断讨论;事既关己,言犹在耳,却置若罔闻。错置的时空,失去的关系,出走的情人─整个剧场,彷彿没有太具体的行动,没有高潮,但处处都是张力矛盾,彷彿翻揭很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又彷彿没有甚么大不了的问题。很多问题,似乎无疾而终。
彼此背叛又探摸
从一开始,编剧像上帝,缔造这场矛盾,把观众置身事外,又彷彿比当事人知道得更多,但这也是观众心理期待最痛苦的所在。两对「偷食」的夫妇于同一晚发生一夜情(其中一对最终悬崖勒马,可是心理上早已出轨)。他们的对白彼此似在唿应、暗示、回答、质询自己,观众或许会产生幻觉,他们在不同空间,在向对面那正出轨的伴侣质询。夫妇之后在一起时,又在彼此探摸与闪躲中,出现了类似的通感和应。再而两男、两女无意中相遇,在建立一种几乎贴近交浅言深的状态,却摸底揭露了对方曾与自己伴侣有一手,这是何等的颓唐。
观众又再一次成为最知情的旁观者,也同样是受骗者,因为编剧似乎没有准备让观众移情投入。大量戏剧对白,表面上跟对手讲话,同时又有点像梦呓般的自言自语,彷彿是向观众敍述自身的对白。可是由于有时角色是在讲述自己的想法,或直觉反应,变相有些部分出现类似对位敍述(counterpoint narration)的情况,像有一种说法,利用人物的想法拉开剧情,拉远焦点,明明现实是冲突失望,却把它搬弄成笑位和错觉的调剂。第三部分,心理医生Valerie的丈夫,是她辅导对象的现任情人。一段三角关系,通过辅导场景和电话留言的交叠呈现,这种近似对位敍述更为明显,自然地淘汰了辅导室场景里的严谨和专业,观众到底要相信谁?这种对角色的嘲弄,对观众心理期待扭转的方法,抵销了本来不真实的巧合和机遇。导演要求演员用怎样的风格演绎对白,亦是十分关键。看过一些外国剧团演绎,有些色慾场面,举手投足,大鸣大放;有些则把人物行动收敛,对话成为主要的内在行动,这便是挑战演员的戏剧感和内在力量的时候。导演在处理时,又会否加插香港当下的背景?把英语对白翻译成港式对白后,怎样保留原文因语序所产生的敍述效果,而不至过于离地?这是对导演和演员的期待,也是这剧本为甚么不断吸引不同地域的剧团翻译并演出的原因。
爱的表达不是一个口号
剧名翻译成《叛侣》,背叛和情人的忠诚,相信就是这次演绎的指涉。爱里必然包括信任,情侣太容易讲爱,却不讲信任,爱和信任是伴侣的「倚天」「屠 龙」,缺一不可。我们不能只宣诸于口而没有真情实感的爱。港人平日听得太多大量政治宣言,人人都说爱香港,这种集结式、口号式的话语,经常缺乏质感。人释出的话语像录音机,没有调整机能,没有接收能量,行为上却是不断的伤害,爱,便无法令人信任。
情绪智商的专家常常鼓励人表达感受、表达爱。前提是,我们先要切切实实懂得自己感受。剧中人忖度情人的爱,怀疑自己爱的分量,或爱本身可以坚持多久,说穿了,是怀疑自己。人类的感受细密和幽微,有时混浊,有时清空,更多时是错综复杂。自己也难于对自己的爱描画清楚,更何况用说话釐清?文学、戏剧的功能(虽然艺术是超功能的,不以功利为本相)也包含这种细腻的捉摸。爱不是从对话发生,亦因为这种难以发生的无色无味,信任更是无法轻易抓紧。所以澳洲导演Ray Lawrence改拍成电影 Lantana,中文译名是《爱情无色无味》就是这个意思。
剧中第二部分是严重的沟通迷障。每个角色把自己的情感或事情的来龙去脉塞给对方或者观众,但任何一方的唿求从未被回应。在他们每个人口中的敍述,都可以是一场场戏剧性行动,但编剧要求演员把戏剧性行动讲出来,而不是演出来,这种失败的沟通,表面上交代剧情或背景,但实际上更加强了吊诡和悬念,这种把对话双方的思绪、挣扎加叠掺和的情况,理性对话额外显得荒谬。社会很多标榜所谓理性对话,但在多元的社会里,理性往往变成否定情绪反应,为情感区域划界线的藉口。缺乏同理心和情感的介入,细緻敏锐的情绪不受尊重,造成更多沟通的障碍。观众多少会从这齣剧体会到,爱和信任、背叛和罪,不能用理性来阐释。正如观赏此剧时,完全理性根本不可能;观众必须想像,对白背后,角色对自己所划的思想界限,他所说的,他也不晓得。
对白演绎内在心理行为
剧名Speaking in Tongues对我来说,自然联想到圣经里的方言。方言的产生来自人类的骄傲,野心建设巴别塔(Tower of Babel),自比天高,与上帝同等。结果上帝改变了人类口音,以方言使人类的沟通再不是必然,必须经过学习。方言的障碍又使人产生无止境的隔阂,直至我们承认个人不能顶替全知全 能的上帝。另一说法,方言是神赐给祂的信徒恩赐,是天使的话语,我们不知道方言在说甚么,只知道使用方言祈祷便可直达天庭。这种神学理解与剧中人的怅惘有点共通,就是彼此言语不通,仿似自言自语也不知自己说甚么,只有爱他的人才读通方言。台湾剧坛曾把此剧译成《言舌》─ 舌头上的言语,谁最清楚?对话,你说变得何等神圣!圣经《雅各书》说,舌头虽然是身体上一个小小的部分,却能大大地自夸。像那么小的火,能点燃那么大的森林!这个剧名和这剧的手法,不知是否想勘探这座森林。
最后,为免剧透,我只能提醒,此剧以对话的内在心理为主线,观众必须学习预备直面几项观戏的挑战:
第一、对白不时对观众情绪和判断加强控制,误导你误判关系,这是另一种背叛本身。所以看任何戏,也不必尽信角色在讲真相。对白是用来引导你进入, 或对抗某种状态。现实如此,戏剧如是;
第二、对话既然不达至沟通的果效,必须承认对白的模煳性和虚假。这个敍述对白抑或戏剧对白难分辨的剧本,独白也好,自言自语也好,对白的非合理性,倒更要期待演员把内心行为演出来,不是讲出来。戏剧如此,现实更加如是。
这齣早在澳洲成名的剧作,会否对当下香港人心释出某些善意的忠告,拭目以待。如果你已经不相信的话,你还有勇气拿出信任,继续面对自己,否决一切用对话包装而拒绝介入情感关注的沟通吗?虽然这是无关宏旨的。
吴美筠
澳洲雪梨大学哲学博士。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创会委员及现任董事、香港文学评论学会创会主席。曾于香港大学、岭南大学等院校任教。香港艺术发展局民选委员及文学委员会主席(2014-2016),现为该局艺术评论委任评审员。2018年香港教育大学驻校作家。出版文学作品多部,着有艺评集《独眼读看─剧场、舞影、文学跨世纪》;编《香港文学的六种困惑》。创办中学生杂志《珍珠奶茶》,深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