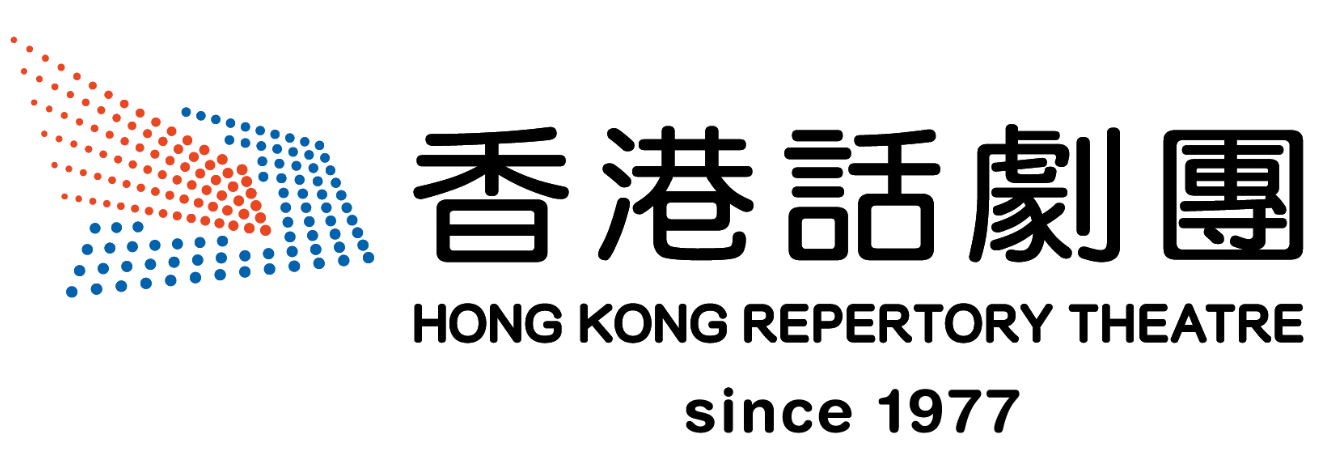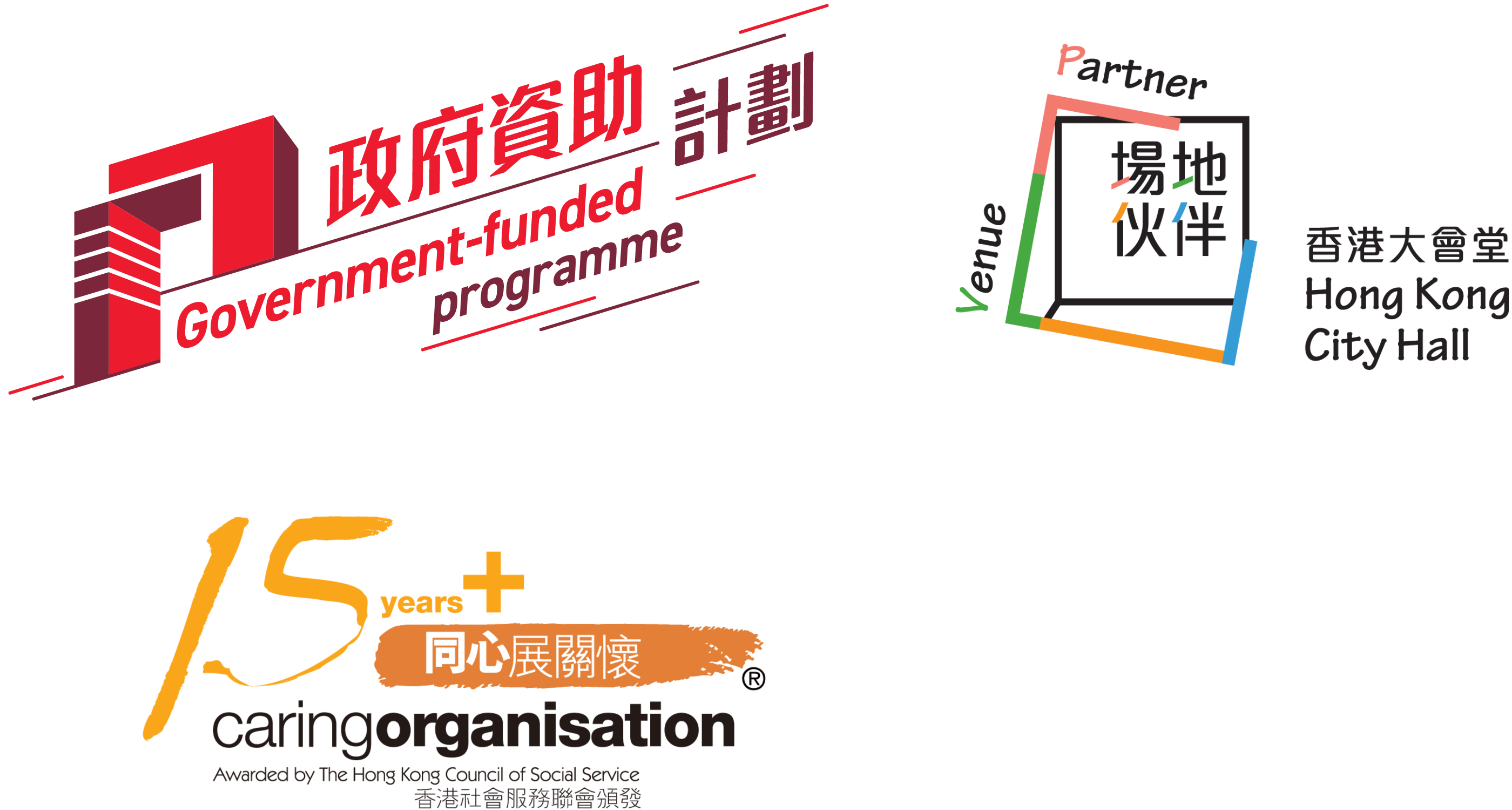「风筝计划」文库
在一个「静默」里看世界「风筝计划」沙龙一 :「拉出你的金线,让风筝起飞」活动纪录
「风筝计划」沙龙一 :「拉出你的金线,让风筝起飞」活动纪录
余香復新「风筝计划」沙龙二:「豁出去,你准备好了吗?」活动纪录
「风筝计划」沙龙二:「豁出去,你准备好了吗?」活动纪录
「风筝计划」的第二节「沙龙」,同样以读剧环节开始,却又有新花样——「流动式读剧」。两位资深剧场工作者陈淑仪和陈丽珠在读剧过程中或有走动、或会谈笑、与观众互动,使台词不再是台词,更是一场真实的日常对话。伴随张蔓姿(Gigi)随性的钢琴音符,《小岛.余香》中那座远离凡俗纷扰的小岛逐渐浮现;苏青、蒋平、或韩三,就在人群之中,转动半空的透明风筝线。
每人手中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线,看不见,却紧扣着生命与尚未诞生的创作。潘Sir希望能在剧场以外的地方和观众谈谈天,使交流不再单向。源于生命的创作,应终归于生命,这亦是「风筝计划」对创作的期许之一。
生活与偶然
「创作,是一种豁出去。方才两位读剧的态度,也是一种豁出去。」《小岛.余香》(原名《小岛芸香》)写于1993年,次年首演,三十年来各剧团搬演不断,也是不少APA学生钟爱的练习之选。
歷久不衰,源于潘Sir的一次「豁出去」。
潘Sir自谦地说,能写出《小岛.余香》这般故事是意料之外。小岛的存在,蒋平和苏青的相遇,角色间的去与留、执与捨,在几个偶然间成就了那段不完结的人生旅途,也展开了属于《小岛.余香》的生命。
创作本就该放胆去写、去试、去把握生活中的每一次触动。潘Sir笑着说:「唯有我们豁出去后,才能创作出有意思的东西。」
众人的芸香余韵
属于剧本的生命,会在每一次的演绎中不断加深、扩散、丰富,渐渐沉淀了缠绕不散的《小岛.余香》。至于各人能感应到的香气,皆略有不同。
陈淑仪喜欢《小岛.余香》的浪漫。这种浪漫来自人与人相处的错位和缘分,是「得不到」方才更显浪漫。而陈丽珠深信《小岛.余香》的“Timeless”,剧中核心并不单是爱情,更是人生。「不説爱情的位反而是在説爱情,」她随口提出几句为例:「每隔一段时候……就有人喺出面经过……但系就没人会好似你咁样,若无其事咁走入嚟……」听到这,潘Sir禁不住笑言:「我在你面前真的是透明的。」或许这就是如实写下自己观察与体会后,观众能读懂并给予回应的美好吧。
有观众形容回忆为一种「让人放不下的toxic」,变成艺术作品后去品味更让人沉迷。那么,「人到底要留着美好还是放下?」。亦有APA毕业生分享当年演读《小岛·余香》时没太大感触,但当生命继续前行,再回首,她终于触碰到《小岛.余香》的另一层香气——人与人的相处和自我探索。
对潘Sir而言,剧中的爱情不过是载体,承载着剧中人物的本质,即人最重要、最坚持、最不能改变和放下的东西。因此《小岛.余香》确实不仅是爱情故事,更是苏青的个人昇华。及后半部,苏青已不再在乎韩三会否回来,她已超越爱情和世俗,确立了独立自足的自我内在价值,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不受外界变迁干扰。
《小岛.余香》是Gigi就读APA时首个帮忙伴奏的剧场演出,驱使她转而踏上音乐之路。在她看来,这个剧本是用爱情包裹着人生百味,放下、拥有、牵绊……每当迷惘时,就翻出这个剧本一再细味,重回小岛,找回纯粹的心境,理清思绪后,再次出发。Gigi直言,人生在世有许多经歷,滋生不尽相同的情绪。即使遇到挫折或不如意,也不要忘却自己最初的纯粹与初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因着生命的一次偶然,潘Sir创作出这座拥有生命力的小岛,浮游于剧场间;由剧中人烘制出的芸香,则已跨越时空,成了众人生命里萦绕不散的余香。
创作不应设限
一个好的剧本应是甚么模样的?该如何寻找标准答案?
当被问到今天重读《小岛.余香》有甚么不一样的感受时,陈丽珠与陈淑仪都不约而同地说,不同演出组合都有其独有的能量,带给他们及观众崭新的感受。陈丽珠指自己在前几天一个无眠的夜晚重阅剧本,发现即使距离上次出演苏青一角已过了六年,仍能记得剧中文字,又是一番感受。而陈淑仪则分享,因应导演或制作的演出处理,虽是同一个剧本,仍能以相同的文字演出不一样的效果。确如Gigi所言,每位演员都有自己的chemistry和energy。潘Sir笔下的《小岛.余香》是苏青和蒋平的一节生命片段,而每位演员饰演的苏青或蒋平或韩三,则在他们融入自我后,调制出独特的新香气。
陈淑仪笑述当年演出时,曾邀请潘Sir讲解《小岛.余香》内容,潘Sir寥寥数句,让淑仪记到现在:「没啊。我写晒架喇。咪咁咯。」「没架,喺晒度喇。你哋自己理解啦。」
在潘Sir心中,剧本并不存在预设的演出画面。写剧本的时候,从不想将来演出的具体模样。每回演出,每对组合,犹如苏青制香,可控不可控。无疑,人可透过精准把控香料份量来寻找最渴望得到的香气,可总素难以控制的影响因素,如天气,令所谓的理想无从达到。因此,潘Sir从不强求几乎不存在于现实中的设想,而是每次都豁出去,把独属那次演出制作的感受牢牢地刻在心里。
优秀剧本应有甚么模样?没有定案。或许未有边界或设限的剧本,是其中一个答案。《小岛·余香》是潘Sir的一次豁出去,但绝非最后一次。与其为创作定型,立下框架,倒不如放出一只翱翔在生活、写满字语的彩色风筝,让它在雨水和阳光的沖洗下展露从未设想的面貌。
总结:豁出去与粤语书写
潘Sir一直秉持「豁出去」的信念完成个人创作,从不考虑任何目标或期望收穫,只单纯地写,做自己觉得应做的事。
风筝计划面向以华文书写的剧作家,希望能鼓励和促成更多本地原创剧本的诞生。对于陈丽珠与陈淑仪等表演艺术家而言,原创剧扎根于相同的文化,不存在因翻译而导致的语言失落,能让他们在没情感落差的状态下进入核心本质。即便已有不少外国优秀剧本可搬演,话剧团依旧着眼于本地剧作,希望能有更多剧本供让本地演员以自己的语言诉説情感与故事。
正如陈丽珠所言,看似简单的广东话句子,背后能有三四层意思。原创剧与翻译剧拥有相近的解读趣味,却更贴近本地生活。唯有零距离、豁出去,真诚地创作,才能如《小岛.余香》般,唤起各位共鸣,焕发出一层一味的芸香,再飘溢到每一吋天空去。
作者简介
陈翠珊(香港话剧团戏剧文学部实习生)
还有一件事「风筝计划」沙龙三:戏剧的正经与怪诞 ——我们为甚么要怪诞?如何怪诞? 活动纪录
「风筝计划」沙龙三:戏剧的正经与怪诞 ——我们为甚么要怪诞?如何怪诞? 活动纪录
(撰文:香港话剧团戏剧文学部)
隔意象的山,打观众的牛「风筝计划」沙龙四:「写One Man Show有几难? ( 或有几易? ) 」
「风筝计划」沙龙四:「写One Man Show有几难? ( 或有几易? ) 」
「点解啲老虎咁贱格嘅呢?」
第四次风筝计划沙龙,潘Sir笑说香港话剧团「很不幸」选读了他这个剧本。这节读剧沙龙的主题是独脚戏,题目为「写One Man Show有几难? ( 或有几易? ) 」,然而《隔山打牛》读剧的演员却有陈健豪、王晓怡两位,到底所为何事?
两个演员,原来分别饰演一个人,一只牛。女演员饰演的「人」,是初出茅炉的男斗牛士;男演员饰演的「牛」,则是无端捲入那不是战胜就是战死的斗争中的大水牛。一人一牛,彼此语言互不相通,无法明暸对方,但他们必须共同度过那应该要互相伤害,却又不知为何互相伤害的「斗牛」时刻,编剧让他们在这情境下剖白内心困惑与人生志向,述说关于生命的千语萬言。
「但系我知道,佢哋唔系为咗搵食……我亲眼见过一只老虎,咬死咗一只羚羊,一啖都没食到,净系喺条羊尸旁边疴咗笃尿,然后若无其事,迓下迓下咁就走咗去……」
剧本缘起,需要追溯至2005年,康文署举办「单.双.男.女」系列节目,目标是制作外国和本地各一男一女演员担纲的独脚戏。香港代表方面,男演员是李镇洲,女演员是邵美君,由潘Sir担任导演和编剧。按照正路的做法,是写两齣独脚戏,让男女演员轮流演出,但潘Sir就是不喜欢正路的做法,所以利用巧妙的戏剧设定,让两位演员的两段独脚戏在同一演出中同时进行,两个角色自说自话,他们的行动与思考却又互相唿应,编织出动人的戏剧表演。
题材上,潘Sir主要从李镇洲旅行所买的书得到启发,那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本书Death in the Afternoon,关于西班牙斗牛歷史和传统;同时亦採用了海明威另一篇短篇小说The Capital of the World,该小说描述了一个在餐厅做侍应的少年梦想成为斗牛士,而少年的侍应同事却嘲笑他,认为他不可能成为斗牛士,他们于是在餐厅找一张椅子,在椅背绑上两把刀演练斗牛情景,期间少年不慎被刀刺中身亡。从这两个作品中,潘Sir得到启发,写成《隔山打牛》。
「我成日都见到猫捉老鼠,螳螂捕蝉,公鸡啄蜈蚣,麻鹰叼鸡仔,蟒蛇搏大象……但系我从未见过一条鱼咬一只虾,又或者一只蟹拑一条吸血虫嘅喎……点解呢?」
以上这段独白,是大水牛「由个太阳坐喺山顶一路谂,谂到个太阳碌左落山腰,都谂唔通」的问题。讲斗牛,却不只是讲斗牛,潘Sir所写的剧本多是如此,而《隔山打牛》还有另一个剧名《最后一道防线》,潘Sir说︰「所谓最后一道防线,是讲人的最后一条底线,是一个尊严的问题,一个自己守住尊严的问题,最后产生了一个悲剧。」
每节沙龙潘Sir都会分享创作的小秘诀,潘Sir这次就与观众分享他自己如何写独白。曾有观众问过他,内心独白的作用多数是回忆过往,那如何判断甚么时候该用独白,甚么时候该用重现的策略呢?潘Sir认为是按戏剧发展情况而定的。当选用了独白,又如何写得好?他在自己剧本选段分析,认为那段是写得「都ok」,「过到自己底线」的独白。原来独白写得好的关键,是要写得有动感,有Action。
「我讲过嘅啦,我由黑草平原打到上黄泥坡,未逢敌手!(打到上黄泥坡,就是action)斑马,老虎,响尾蛇,通通都系我嘅手下败将!(有股力量,最重要是有一股激情)只有两次失过手,一次系俾一只无耻嘅红火蚁偷袭(action),咬咗我屎忽一啖(action),另一次就系俾一班下流嘅乌鸦围剿(action),啄咗我左眼一嘢(action),但条我已经学精咗啦,喺荒野里面生存(渴望生存),唔系你死就系我亡(有passion),点可以唔学精㗎?所以嗰啲蠢牛咪死晒啰,牛蠢真系没药医㗎,一只牛点解会蠢呢?(问题,问题必然是期待答案,这也是一个action)原因只有一个,就系唔识得思考啰(思考,是一个action),我成日同嗰班契弟讲,我话你哋唔想死(这是愿望,是desire)就好似我咁,得闲用下个脑啦(action),点解我哋有两只角,啲狮子老虎没㗎?(提出问题,撩起观众期待答案)剩系呢个问题,我都谂咗三个春天(一个suspension!那答案是甚么?),而家终于俾我谂通咗啦,狮子老虎唔系没角,只不过,佢哋嗰两只角,生咗落棚牙嗰度,所以佢哋有两只特别尖,特别长嘅牙(有种insight……很有想像力,也有牛的观点,在一段独白,action、action、desire、insight,有独特的看法,这样就构成一段能够吸引观众,或者它本身是有趣的独白,这就是底线,起码它是有趣的),就系咁解啰,呢啲嘢你唔谂边个话俾你知呀?唔知(后果很严重,会死!)你咪死梗啰,死唔紧要,但系唔好死得不明不白丫嘛,啲狮子老虎唔系用两只牙咬死你㗎,佢哋系用两只角插死你㗎(哗,有insight),蠢材!(这只牛,很有insight,这就是一个好的独白)」[1]
在演艺学院读编剧的这一年,深刻记得潘Sir说戏剧与其他艺术媒介不同,在于戏剧是show(呈现),而不是tell(说明)。「我想你们留下来都是想知道我这齣戏到底想讲甚么,但不好意思,我不会告诉你的。」在演后谈,潘Sir如是说了,但最后还是跟大家分享︰「那只牛和那个少年都被置放在一个无法后退的处境,他们唯有面对眼前的事情……也因此能够谈到比较哲学性的东西,例如生存、死亡等形而上的东西。」而那个形而上的东西,很多时候是无法说明,只能呈现并让观众去感受,纵使独白是说出来的,精粹还是透过文字与言语呈现一个世界。
笔者最喜欢本文多次节录的那段独白,它的结尾是关于覆盖在狒狒尸体上的乌蝇,那些狒狒是无缘无故被老虎咬死的,独白其中一句︰「我心谂……一亿只乌蝇,拼贴成一张完美无瑕嘅裹尸布,都算系一个极之隆重嘅葬礼啦……但系我唔明……点解一只老虎要做一样咁样嘅嘢呢?」潘Sir说这段独白的意象贴近他想探讨的哲学命题,老虎杀羚羊、狒狒的原因是甚么?「以我自己为例,有时候也不知为甚么,做了一些事情而令人伤心。我出发点是甚么?我为甚么要做这件事?我做这件事有甚么好处?可能是找不到答案的,可能在我们本能中是有一些所谓的黑暗面。这齣戏是通过这些意象,这些独白,来提这些问题。」
[1] 编按:此段落中括弧内的字句为潘Sir的点评。
作者简介
胡筱雯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主修政治及行政学,副修新闻及传播学;现时为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生,主修编剧。
于2020至2022年任职《明报》文化版记者,并获得2021年香港最佳新闻奖最佳文化艺术新闻报道优异奖。现为独立艺文记者,曾于《香港独立媒体》、《18/22》等媒体撰写专访;亦曾为M+、不加锁舞踊馆等机构及团体撰写专访文章,文章刊登于《经济日报》、《虚词》等平台。
一张前往春威夷的车票「风筝计划」沙龙五:《K城以外二三事》 ——「叙事的想像和想像的叙事」活动纪录
「风筝计划」沙龙五:《K城以外二三事》 ——「叙事的想像和想像的叙事」活动纪录
玻璃墙外游人向内张望,墙内有人独坐,情侣依偎在沙发上,也有分手不久的男人携新女伴入场。因着偶然,与陌生人在浪漫的地点共度难以言喻的时光。
[……][1]
手提电话又是一项讨厌的发明。每当我在公众场所听到有人大大声讲手提电话,心里就开始咀[诅]咒,愿他的手提电话漏电,把他电哑。
观众回应,这次在公开场合朗读私密的小说,更能够凸显文字的力量,也提醒人们反思自身。潘Sir则举作品《李逵的蓝与黑》和《武松日记》为例,深信文字在舞台上产生的力量,「只要文字处理得好,演员传递得好,便不会觉得闷。」话剧团启动风筝计划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唤醒大众对文字和剧本的关注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