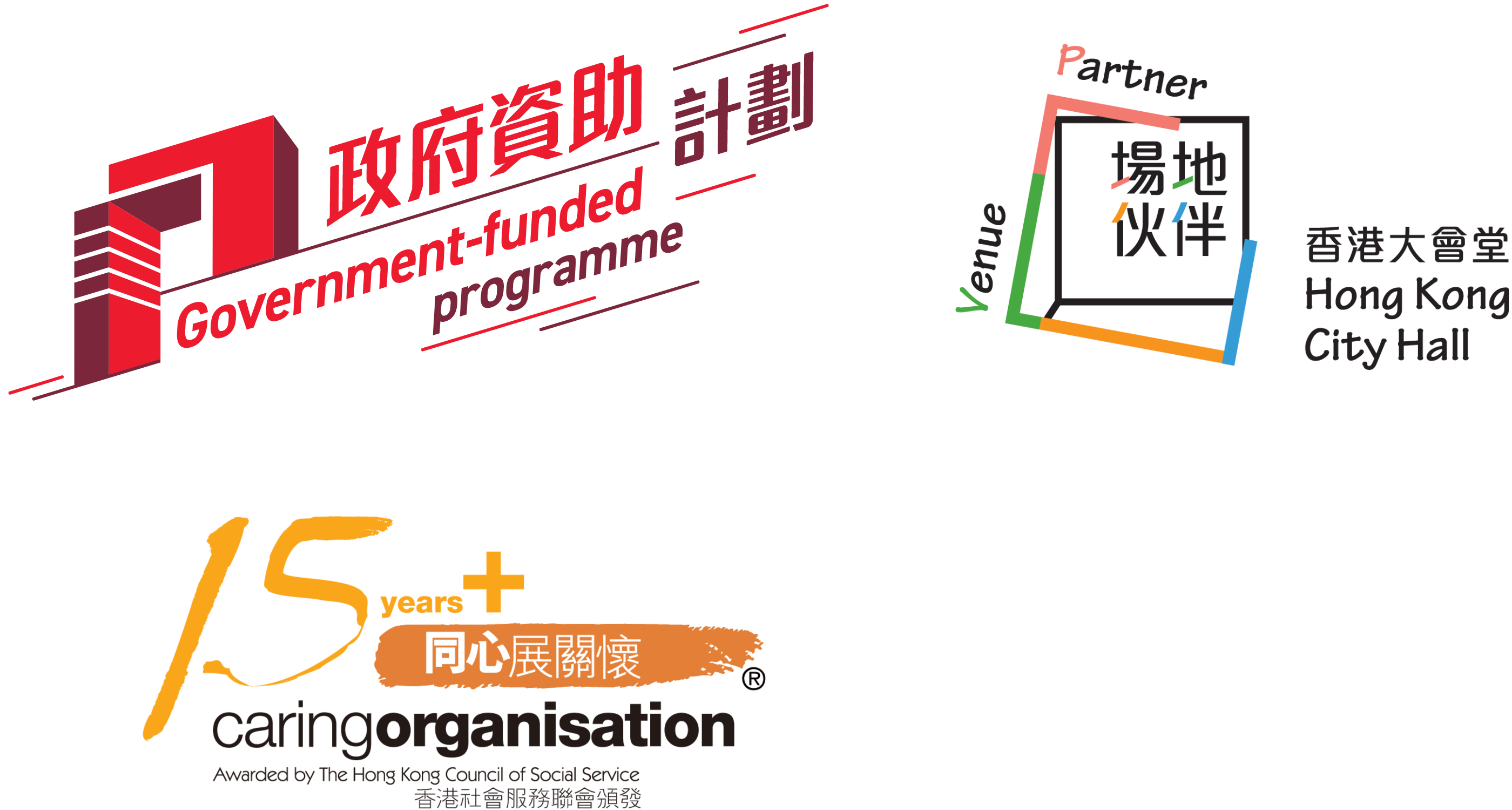2024-25年度「风筝计划」编剧眼中的编剧
09.03.2025
2024-25年度「风筝计划」公开演读
编剧眼中的编剧
2024-25年度「风筝计划」从近百份华文剧本投稿中,精选八部作品进入公开演读阶段。这些作品风格迥异,涵盖从两人密室的心理博弈,到充满奇幻想像的未来场景;从古人传记的新编重构,到挑战生活的现实隐喻,每一部作品都如同一颗尚待雕琢的宝石。
特别策划的栏目「编剧眼中的编剧」,邀请八位在读或新晋编剧,以他们的创作视角和生活体悟,剖析这些作品的内在魅力与剧作人的巧思。剧作者们的解读不仅是对文本的探索,更是一场编剧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希望藉此点燃更多人对剧本创作的热诚,让更多优秀的编剧以及其原创剧目得以被发现,像风筝般翱翔。
一月:花里看世界
《忘年》:一场有关距离与成长的历程「风筝计划」一月 公开演读《忘年》纪录文章
「风筝计划」一月 公开演读《忘年》纪录文章
《忘年》为香港话剧团2024-25年度「风筝计划」入选的原创剧本之一,编剧为林泽铭,这次以剧本演读的形式展现于观众面前。
故事讲述60年代生的Daniel(DT),与90年代生的Daniel(DK)一段相差三十一年的忘年恋,在不同的人生历程中,追求同步却永不同步的故事。到底,人生之中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同步呢?
(1) 起步点差距的三十一年与不断前进的十五年零六个月
DT与DK两人年龄差距三十一年,而剧本横跨十五年六个月。笔者觉得剧本彷佛把两个角色放在一条时间在线,一前一后,两者不断向前行,而观众期待的,就是两人最终是否能够在时间在线相遇。
事实上,剧本在第一场就透过两人的对话,表面在讨论性,而实际上就是暗示出剧本的核心:
在两人相处的十五年零六个月里,两人分别经历了人生不同的课题。成熟的DT经历了与相处多年的同性伴侣分开、退休、移居、年老到伴侣患病;年轻的DK则经历了学生会事件、朋友离世、理想幻灭、亲人老去、身患重病到养子逝世。两人人生当中经历大大小小的课题,而这些安排亦足见编剧的巧思。DT曾经说过:
但在编剧的安排下,两人人生的经历却刚刚相反,这不禁令人反思:这些有关年龄的种种「理所当然」又是否必然呢?又是否年老的一定比年轻的经历得多?实际年龄是否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唯一指标?也许正如DK在剧中所言:「唔系大啲嗰个先会阻住人同拖累人。边个大啲边个细啲,其实都冇分别。」
有趣的是,去到剧本的最后,面对养子的离世,DT与DK依然有不同的态度,DT离开,DK多年后仍未能释怀,两人的距离或许拉近了,但彷佛依然未能同步。而这又带出一个问题:两个人相处是否必然需要同步、是否必需要同在呢?或许正如剧中的DT与DK一样,互相陪伴着大家经历不同的人生课题,或许会在不同的时段消失,但是又会在不同的时间点重遇,这不是已经很足够吗?
(2) DK:一个少年的成长故事
除了DK与DT两人的关系外,剧本对DK这个少年亦有深刻的描述。DK在剧本之初是一个充满自信、对生活有要求,理想满满的少年,对战争、革命、政变、军事充满兴趣,认为这样才可以知道「啲老嘢点样 fuck up 呢个世界」。
但是当他经历人生的种种生离死别,面对社会现实,昔日主动放弃学位的他要再次考取学历,希望可以在博物馆争取更高的职位,面对关于「战争、革命、政变、军事」的相片时,不断自我怀疑,开始对自己一直以来的价值观产生疑惑。一场一场地看着DK改变,观众彷佛与DK一同经历了一段少年的成长史。
而最令笔者触动的是剧本的结尾,两人多年后重新谈到养子的死亡,DT不禁悲从中来,蜷缩在墓碑前,崩溃似地哭了起来,然后DK对DT说:「真系冇嘢喎。系咁㗎喎。呢啲嘢,好正常㗎喎。」昔日的少年已经三十多岁,也许明白到人生的生离死别,但是明白不代表接受,亦不代表放下。编剧这一笔充满着人生的况味。
(3) 编剧的挑战与巧思
在演后座谈会中,编剧林泽铭表示,剧本其中一个希望达到的,是每一场都不要提及当中的时间,让观众在角色的对话与表现中感受时间的流逝。这令笔者想起Patrick Marber的Closer以及Harold Pinter的Betrayal,两者同样模糊了场与场之间过度了的时间,透过角色之间的关系等线索暗示时间的流逝。
这种处理方法可以带来观赏的趣味,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造成混乱。而笔者认为编剧这次的处理是有效的。编剧在剧本中运用了不少巧思来暗示时间的流逝,例如DK开始有视力问题,需要带眼镜;DK因为健康问题,吃朱古力时要抄下当中的卡路里;儿童游乐场与大厦的拆卸等。编剧成功透过人物与环境的改变,暗示时间的流动。
编剧亦善于运用情景,象征人物的关系及状况。例如第六场在博物馆关灯后,在一片黑暗之中DK亮起手电筒,与DT一同离去,就暗示着DT陪同DK渐渐走出人生黑暗。又例如第八场,DT远在加拿大与身处香港的DK进行实时视像通讯,讯号的接收不良,彷佛就暗示着两人接触不良,不能同步的人生阶段。
所以笔者认为,《忘年》是人物形象丰富、具内容深度并且技巧上充满巧思的作品,就像灵动的风筝,令人期待它越飞越高,让更多的观众可以看到。
黎曜铭
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于2020年获得第六届青年编剧剧本写作计划季军。
写剧本,剧场作品包括香港话剧团《人间》、《初三》;剧场空间《Ellie, My Love》(获第十四届香港小剧场奖最佳剧本提名)、《隐身的X》;影话戏《灰姑娘と金阁寺》、《扣题》、《疗养院的730天》;普剧场《怪の物语》、《怪物》、《彼德与影子的奇幻之旅》。
故事讲述60年代生的Daniel(DT),与90年代生的Daniel(DK)一段相差三十一年的忘年恋,在不同的人生历程中,追求同步却永不同步的故事。到底,人生之中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同步呢?
(1) 起步点差距的三十一年与不断前进的十五年零六个月
DT与DK两人年龄差距三十一年,而剧本横跨十五年六个月。笔者觉得剧本彷佛把两个角色放在一条时间在线,一前一后,两者不断向前行,而观众期待的,就是两人最终是否能够在时间在线相遇。
事实上,剧本在第一场就透过两人的对话,表面在讨论性,而实际上就是暗示出剧本的核心:
DK: 总之全晚我哋就会系咁等到对方得为止。我得嘅时候你又唔得,你得嘅时候我又唔得,永远都冇可能同步。
DT: 咁今日等唔到,咪听日啰。
在两人相处的十五年零六个月里,两人分别经历了人生不同的课题。成熟的DT经历了与相处多年的同性伴侣分开、退休、移居、年老到伴侣患病;年轻的DK则经历了学生会事件、朋友离世、理想幻灭、亲人老去、身患重病到养子逝世。两人人生当中经历大大小小的课题,而这些安排亦足见编剧的巧思。DT曾经说过:
「你第时搭得最多嘅会系飞机,因为你会想周围去,而我搭得最多嘅会系巴士因为有两蚊。你会不断有朋友嘅婚礼要去,而我只会系咁去朋友嘅葬礼。」
但在编剧的安排下,两人人生的经历却刚刚相反,这不禁令人反思:这些有关年龄的种种「理所当然」又是否必然呢?又是否年老的一定比年轻的经历得多?实际年龄是否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唯一指标?也许正如DK在剧中所言:「唔系大啲嗰个先会阻住人同拖累人。边个大啲边个细啲,其实都冇分别。」
有趣的是,去到剧本的最后,面对养子的离世,DT与DK依然有不同的态度,DT离开,DK多年后仍未能释怀,两人的距离或许拉近了,但彷佛依然未能同步。而这又带出一个问题:两个人相处是否必然需要同步、是否必需要同在呢?或许正如剧中的DT与DK一样,互相陪伴着大家经历不同的人生课题,或许会在不同的时段消失,但是又会在不同的时间点重遇,这不是已经很足够吗?
(2) DK:一个少年的成长故事
除了DK与DT两人的关系外,剧本对DK这个少年亦有深刻的描述。DK在剧本之初是一个充满自信、对生活有要求,理想满满的少年,对战争、革命、政变、军事充满兴趣,认为这样才可以知道「啲老嘢点样 fuck up 呢个世界」。
但是当他经历人生的种种生离死别,面对社会现实,昔日主动放弃学位的他要再次考取学历,希望可以在博物馆争取更高的职位,面对关于「战争、革命、政变、军事」的相片时,不断自我怀疑,开始对自己一直以来的价值观产生疑惑。一场一场地看着DK改变,观众彷佛与DK一同经历了一段少年的成长史。
而最令笔者触动的是剧本的结尾,两人多年后重新谈到养子的死亡,DT不禁悲从中来,蜷缩在墓碑前,崩溃似地哭了起来,然后DK对DT说:「真系冇嘢喎。系咁㗎喎。呢啲嘢,好正常㗎喎。」昔日的少年已经三十多岁,也许明白到人生的生离死别,但是明白不代表接受,亦不代表放下。编剧这一笔充满着人生的况味。
(3) 编剧的挑战与巧思
在演后座谈会中,编剧林泽铭表示,剧本其中一个希望达到的,是每一场都不要提及当中的时间,让观众在角色的对话与表现中感受时间的流逝。这令笔者想起Patrick Marber的Closer以及Harold Pinter的Betrayal,两者同样模糊了场与场之间过度了的时间,透过角色之间的关系等线索暗示时间的流逝。
这种处理方法可以带来观赏的趣味,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造成混乱。而笔者认为编剧这次的处理是有效的。编剧在剧本中运用了不少巧思来暗示时间的流逝,例如DK开始有视力问题,需要带眼镜;DK因为健康问题,吃朱古力时要抄下当中的卡路里;儿童游乐场与大厦的拆卸等。编剧成功透过人物与环境的改变,暗示时间的流动。
编剧亦善于运用情景,象征人物的关系及状况。例如第六场在博物馆关灯后,在一片黑暗之中DK亮起手电筒,与DT一同离去,就暗示着DT陪同DK渐渐走出人生黑暗。又例如第八场,DT远在加拿大与身处香港的DK进行实时视像通讯,讯号的接收不良,彷佛就暗示着两人接触不良,不能同步的人生阶段。
所以笔者认为,《忘年》是人物形象丰富、具内容深度并且技巧上充满巧思的作品,就像灵动的风筝,令人期待它越飞越高,让更多的观众可以看到。
作者简介
黎曜铭
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于2020年获得第六届青年编剧剧本写作计划季军。
写剧本,剧场作品包括香港话剧团《人间》、《初三》;剧场空间《Ellie, My Love》(获第十四届香港小剧场奖最佳剧本提名)、《隐身的X》;影话戏《灰姑娘と金阁寺》、《扣题》、《疗养院的730天》;普剧场《怪の物语》、《怪物》、《彼德与影子的奇幻之旅》。
《钢牙无爪》:戴一世的retainer「风筝计划」一月 公开演读《钢牙无爪》纪录文章
「风筝计划」一月 公开演读《钢牙无爪》纪录文章
受牙痛折磨的女子,夜晚赶到牙医诊所求医,本来已经下班的牙医再三拒绝诊症,岂料发生连串意料之外的事,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被逼困在诊所里,面面相觑,由此展开剧情。
剧本结构简单,没有太刻意、花巧的设计,封闭的空间,时间幅度定在一个晚上,单靠两个人物之间看似日常琐碎的对话推进,难度匪浅,剧本却可以流畅自然地带出少女的「牙痛」心事。
编剧将女生角色设置成一个傻更更的少女,经常自说自话,甚至有时候有点脱离现实。当牙医打发女生离开,着她明早来,安排一个免费的检查,当是错手整烂retainer (牙齿固定器)的赔偿,女生不从,坚持指控牙医是黑帮,以牙医之名行非法活摘人体器官之实!剧本中的女生就是这样一个带点粗线条的角色,而活到中年的牙医又是一个看重自己专业,对一双「灵巧的手」引以为傲的角色,把箍牙是「一种对美的追求」奉为圭臬。
在这个角色排列组合下,有时针锋相对,互不咬弦;有时二人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错开对话,而突然之间,又会因着一些语言上的错位而碰撞,迸发出连番趣味。编剧间中加插广东话「食字」的冷笑话 ,例如:牙医吃火锅,女生提醒他食材未熟,牙医脑筋急转弯,向女生自我介绍之后道出的一句,「而家熟咗啦」,二人终于真正的对话,暗示两人关系逐渐走近。看着二人招架对方,也是挺过瘾的。
可惜的是,有时候编剧把握到人物在某个处境而引起的笑位,但未有在此之上刻划人物重要面向。例如,牙医二十四小时生活在诊所,无论上班下班,他戏谑这种生活方式是work from home ,其实正正对应着剧本中描述疫情时期的处境,好一个幽默。
不过幽默归幽默,到底牙医是怎样看待生活、关系,以至外面的世界呢?为甚么他选择全天候居住在诊所?是因为经历感情挫败和前妻去世,创伤之后的逃遁吗?抑或一如女生所料,牙医除了专业资格以外,生活无甚嗜好,日日都百无聊赖?剧本未有足够的提示,只有牙医轻轻带过的一句,「一离开咗间诊所,就咩都唔系,咩都做唔到」。
对比之下,女生的角色有相当的着墨,少女心事亦成功扣连在「牙痛」的意象。牙齿作为全剧的骨干,去到第三场才逐渐浮现,揭露角色欲望。女生箍牙之后,中间有五年没有按指示戴retainer ,结果令牙齿移位。现在的她,执着还原七年前箍好牙的完美模样,渴望将最靓最好的自己送给男朋友。就在这一晚,男朋友向自己提出分手,令女生发现,要戴足一世的retainer 始终无办法箍住一段变幻无常的感情关系,牙齿会走样,关系亦然。女生强行将retainer 戴在已经不再如初的牙齿上,这份执着正正是造成她牙痛的肇因。以「牙痛」作喻,穿连起率真可爱的少女爱情观。
牙医的爱情观,大抵就是见于他提及过的前妻,和帮她箍牙后的灿烂笑容,而他抗拒新式隐形牙箍,坚持用传统钢线牙箍,与客人建立信任与关系,似乎意有所指,但未明确指出。牙医角色点点散落在剧本各处,却欠缺一道针线把牙医每一点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都穿起来。既然全剧以「牙痛」为起点,实写关系,那么牙医这个身分,如何与整个剧本的骨干拉上关系呢?笔者下笔之际,依然在思考编剧经营角色的心思。如果可以更深刻挖掘角色的往事,使他们更立体,相信在剧本的收尾,两个角色的转变时机亦不会过于突兀。
张沚铃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一级荣誉),副修文化管理。现就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课程,主修编剧。
在剧场默默耕耘,暂时结果实的:香港艺术节@大馆《那些巨大与微小的》(2024)制作演出盒子及演出;曾与创作伙伴共同制作纪实剧场《N个自言自语的人》(2023),担任文字整理及创作。于前进进戏剧工作坊「读剧马拉松2023世代变奏 :Millennial 」(2023)节目中担任英国文本《一了百了》(Anatomy of a Suicide)翻译。
剧本结构简单,没有太刻意、花巧的设计,封闭的空间,时间幅度定在一个晚上,单靠两个人物之间看似日常琐碎的对话推进,难度匪浅,剧本却可以流畅自然地带出少女的「牙痛」心事。
编剧将女生角色设置成一个傻更更的少女,经常自说自话,甚至有时候有点脱离现实。当牙医打发女生离开,着她明早来,安排一个免费的检查,当是错手整烂retainer (牙齿固定器)的赔偿,女生不从,坚持指控牙医是黑帮,以牙医之名行非法活摘人体器官之实!剧本中的女生就是这样一个带点粗线条的角色,而活到中年的牙医又是一个看重自己专业,对一双「灵巧的手」引以为傲的角色,把箍牙是「一种对美的追求」奉为圭臬。
在这个角色排列组合下,有时针锋相对,互不咬弦;有时二人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错开对话,而突然之间,又会因着一些语言上的错位而碰撞,迸发出连番趣味。编剧间中加插广东话「食字」的冷笑话 ,例如:牙医吃火锅,女生提醒他食材未熟,牙医脑筋急转弯,向女生自我介绍之后道出的一句,「而家熟咗啦」,二人终于真正的对话,暗示两人关系逐渐走近。看着二人招架对方,也是挺过瘾的。
可惜的是,有时候编剧把握到人物在某个处境而引起的笑位,但未有在此之上刻划人物重要面向。例如,牙医二十四小时生活在诊所,无论上班下班,他戏谑这种生活方式是work from home ,其实正正对应着剧本中描述疫情时期的处境,好一个幽默。
不过幽默归幽默,到底牙医是怎样看待生活、关系,以至外面的世界呢?为甚么他选择全天候居住在诊所?是因为经历感情挫败和前妻去世,创伤之后的逃遁吗?抑或一如女生所料,牙医除了专业资格以外,生活无甚嗜好,日日都百无聊赖?剧本未有足够的提示,只有牙医轻轻带过的一句,「一离开咗间诊所,就咩都唔系,咩都做唔到」。
对比之下,女生的角色有相当的着墨,少女心事亦成功扣连在「牙痛」的意象。牙齿作为全剧的骨干,去到第三场才逐渐浮现,揭露角色欲望。女生箍牙之后,中间有五年没有按指示戴retainer ,结果令牙齿移位。现在的她,执着还原七年前箍好牙的完美模样,渴望将最靓最好的自己送给男朋友。就在这一晚,男朋友向自己提出分手,令女生发现,要戴足一世的retainer 始终无办法箍住一段变幻无常的感情关系,牙齿会走样,关系亦然。女生强行将retainer 戴在已经不再如初的牙齿上,这份执着正正是造成她牙痛的肇因。以「牙痛」作喻,穿连起率真可爱的少女爱情观。
牙医的爱情观,大抵就是见于他提及过的前妻,和帮她箍牙后的灿烂笑容,而他抗拒新式隐形牙箍,坚持用传统钢线牙箍,与客人建立信任与关系,似乎意有所指,但未明确指出。牙医角色点点散落在剧本各处,却欠缺一道针线把牙医每一点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都穿起来。既然全剧以「牙痛」为起点,实写关系,那么牙医这个身分,如何与整个剧本的骨干拉上关系呢?笔者下笔之际,依然在思考编剧经营角色的心思。如果可以更深刻挖掘角色的往事,使他们更立体,相信在剧本的收尾,两个角色的转变时机亦不会过于突兀。
作者简介
张沚铃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一级荣誉),副修文化管理。现就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课程,主修编剧。
在剧场默默耕耘,暂时结果实的:香港艺术节@大馆《那些巨大与微小的》(2024)制作演出盒子及演出;曾与创作伙伴共同制作纪实剧场《N个自言自语的人》(2023),担任文字整理及创作。于前进进戏剧工作坊「读剧马拉松2023世代变奏 :Millennial 」(2023)节目中担任英国文本《一了百了》(Anatomy of a Suicide)翻译。
《旷野》:一趟没有目的地的旅程「风筝计划」一月 公开演读《旷野》纪录文章
「风筝计划」一月 公开演读《旷野》纪录文章
一个孩子自杀的原因会是什么?《旷野》认为,不回答这个问题才是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悼念。《旷野》以非线性的结构,淡然含蓄的语言以及诸多写意的手法讲述一对已离婚的男女发现女儿自杀后,逐渐坦诚自我,与自己、对方以及女儿和解,找到「带上女儿继续生活」的方式,这一个过程。
第三视角看自杀
不同于许多从自我视角,在「自杀之前」切入「自杀」问题的戏剧,《旷野》从他者视角观察「自杀之后」接续的故事。大量从自我视角讨论「自杀」的戏剧大篇幅刻画角色自杀的原因,展露戏剧对人类精神状态问题的关注。美京剧作家Marsha Norman的《晚安,妈妈》(Night, Mother)是一个女儿自杀前与母亲的临终谈话记录 ─ 这些对话揭露了形塑女儿「自杀」这一决定的过往人生:她婚姻失败,和家人朋友关系疏远,患有癫痫让她完全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英京剧作家Sarah Kane的《4.48精神崩溃》(4.48 Psychosis)中支离破碎的语言折射出主角与俗世毫不兼容的自我是她选择离开的原因。
以「女儿自杀」为背景的《旷野》未有点明女儿自杀的原因。编剧认为,当事人的消亡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过去,所以自杀原因不影响当下和未来。另外,人生不一定会有明确的答案。对于男女主角而言,女儿自杀的原因就是他们人生中不可能被解答的谜。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所以他者对当事人的认知和当事人对自我的认知永远存在差距。当事人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自杀,但他者可能无从认知到,所以他者必然对当事人产生的变化甚至毁灭感到迷惘。人们遇到人生中不可知,不可控的变化,找不到变化的原因是人不可能以全知视角看待他人。所以,女儿自杀的原因没有任何他者,包括男女主角、编剧以及观众知道。这不是一部关注「自杀之前」的社会问题或心理分析剧,而意图探讨当事人「自杀之后」,他人如何怀着此事继续前行。这才是自杀一事给他者带来的重要课题。
演员和角色设置中的写意特征
《旷野》写明由同一男演员扮演一个男人的多个不同身份以及这个男人的岳父,并由同一女演员扮演一个女人的不同身份、她的女儿以及她的情敌。编剧认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不同的身份,处于不同身份对应的不同关系中。剧中有些角色不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仅仅因为性别一致就被同一个演员演绎,因为人物不仅受到自己的过往影响,还受自己未曾参与的过往塑造。编剧让女演员同时饰演女人和第三者,能表明女人如今对男人的怨恨和隔阂源自于男人和第三者的婚外情。女人的父亲和丈夫由同一男演员饰演,暗示女人的父女关系和婚姻关系对她施加了类似的影响,共同造成女人目前的心理状态。女人的父亲和丈夫在离开女人时都没有给女人明确的答案。同样的不告而别屡次发生,女人逐渐接受这一事实,在面对女儿的离去时决定不再穷求人生的答案,而是带着未解决的记忆前行。所以虽然她还是在意男人曾经犯的错误,但她不再要求男人明确响应她这些事,就可以回家悼念女儿,毕竟,这里「总归是他家」。两名主角,亦即自杀女儿父母过往岁月里不同的人物以及人物们背后的过往,共同塑造了他们的当下。
在意识中潜行的旅程
《旷野》的叙事结构表明探索生命问题是钩沉过往的过程。《旷野》不同场次讲述不同时段的过往记忆。这些记忆片段不按时间顺序展现。比如第四场的情节发生于女儿青春期,第五场的时间点跳回母亲少女时期,而第六场的时间又跳到女儿青春期。非线性的叙事结构里,场次铺排看似随意,却符合意识活动的跳跃特征。
全剧中,角色并未开展新行动或者以冲突推动情节发展。他们的唯一行动就是发掘过往记忆。过往的某些记忆已经存在,只是长期封存在心底,需要契机唤起。不同记忆片段隐藏在主角的过往里,作为他们对女儿自杀成因的多种猜测方式,在这趟回忆旅程里被拾起,拼凑,呈现主角从未意识到的,人生的真实面目。例如,父亲翻动女儿的遗物时,找到女儿小时候为他煮雪糕时用的匙羹,想起自己的父爱之情第一次被唤醒的时刻。开场时一直紧闭心门的男人此刻不由自主暴露了自己的真情,令女人也暂时放下因他的婚外情和离去而出现的情感隔阂,由衷地安慰男人,欢迎他归来。因为男人的真情流露让她又回到了一切事端尚未发生时,和这个男人渐行渐远之前。这时她才格外强烈地感觉到,原来在她心里,不管自己和男人的关系怎么变化,其实他们一家三口永远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不能分离。
总结
独特的生命观念令此剧否决对确定性的追寻。女儿到底为什么自杀,舞台上的女人到底是女人自己还是女儿还是第三者,一场戏结束后,故事会跳到时间在线的哪个地方,答案都不清晰。但正是这种不清晰令《旷野》高度符号化且具有开放性,令人搁置对某一独立确定通路的追求,接受人生就是旷野,哪里都是出路,但哪里都雾气蒙蒙,无边无际。
何其乐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就读香港大学文学及文化研究硕士课程。曾参与改编《风尘里》、《女刑警队长》等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以及上海静安戏剧谷、上海国际喜剧节的策划工作,长期为剧情类自媒体账号供稿。创作舞台剧剧本《洞》及《恨逝》。
第三视角看自杀
不同于许多从自我视角,在「自杀之前」切入「自杀」问题的戏剧,《旷野》从他者视角观察「自杀之后」接续的故事。大量从自我视角讨论「自杀」的戏剧大篇幅刻画角色自杀的原因,展露戏剧对人类精神状态问题的关注。美京剧作家Marsha Norman的《晚安,妈妈》(Night, Mother)是一个女儿自杀前与母亲的临终谈话记录 ─ 这些对话揭露了形塑女儿「自杀」这一决定的过往人生:她婚姻失败,和家人朋友关系疏远,患有癫痫让她完全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英京剧作家Sarah Kane的《4.48精神崩溃》(4.48 Psychosis)中支离破碎的语言折射出主角与俗世毫不兼容的自我是她选择离开的原因。
以「女儿自杀」为背景的《旷野》未有点明女儿自杀的原因。编剧认为,当事人的消亡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过去,所以自杀原因不影响当下和未来。另外,人生不一定会有明确的答案。对于男女主角而言,女儿自杀的原因就是他们人生中不可能被解答的谜。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所以他者对当事人的认知和当事人对自我的认知永远存在差距。当事人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自杀,但他者可能无从认知到,所以他者必然对当事人产生的变化甚至毁灭感到迷惘。人们遇到人生中不可知,不可控的变化,找不到变化的原因是人不可能以全知视角看待他人。所以,女儿自杀的原因没有任何他者,包括男女主角、编剧以及观众知道。这不是一部关注「自杀之前」的社会问题或心理分析剧,而意图探讨当事人「自杀之后」,他人如何怀着此事继续前行。这才是自杀一事给他者带来的重要课题。
演员和角色设置中的写意特征
《旷野》写明由同一男演员扮演一个男人的多个不同身份以及这个男人的岳父,并由同一女演员扮演一个女人的不同身份、她的女儿以及她的情敌。编剧认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不同的身份,处于不同身份对应的不同关系中。剧中有些角色不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仅仅因为性别一致就被同一个演员演绎,因为人物不仅受到自己的过往影响,还受自己未曾参与的过往塑造。编剧让女演员同时饰演女人和第三者,能表明女人如今对男人的怨恨和隔阂源自于男人和第三者的婚外情。女人的父亲和丈夫由同一男演员饰演,暗示女人的父女关系和婚姻关系对她施加了类似的影响,共同造成女人目前的心理状态。女人的父亲和丈夫在离开女人时都没有给女人明确的答案。同样的不告而别屡次发生,女人逐渐接受这一事实,在面对女儿的离去时决定不再穷求人生的答案,而是带着未解决的记忆前行。所以虽然她还是在意男人曾经犯的错误,但她不再要求男人明确响应她这些事,就可以回家悼念女儿,毕竟,这里「总归是他家」。两名主角,亦即自杀女儿父母过往岁月里不同的人物以及人物们背后的过往,共同塑造了他们的当下。
在意识中潜行的旅程
《旷野》的叙事结构表明探索生命问题是钩沉过往的过程。《旷野》不同场次讲述不同时段的过往记忆。这些记忆片段不按时间顺序展现。比如第四场的情节发生于女儿青春期,第五场的时间点跳回母亲少女时期,而第六场的时间又跳到女儿青春期。非线性的叙事结构里,场次铺排看似随意,却符合意识活动的跳跃特征。
全剧中,角色并未开展新行动或者以冲突推动情节发展。他们的唯一行动就是发掘过往记忆。过往的某些记忆已经存在,只是长期封存在心底,需要契机唤起。不同记忆片段隐藏在主角的过往里,作为他们对女儿自杀成因的多种猜测方式,在这趟回忆旅程里被拾起,拼凑,呈现主角从未意识到的,人生的真实面目。例如,父亲翻动女儿的遗物时,找到女儿小时候为他煮雪糕时用的匙羹,想起自己的父爱之情第一次被唤醒的时刻。开场时一直紧闭心门的男人此刻不由自主暴露了自己的真情,令女人也暂时放下因他的婚外情和离去而出现的情感隔阂,由衷地安慰男人,欢迎他归来。因为男人的真情流露让她又回到了一切事端尚未发生时,和这个男人渐行渐远之前。这时她才格外强烈地感觉到,原来在她心里,不管自己和男人的关系怎么变化,其实他们一家三口永远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不能分离。
总结
独特的生命观念令此剧否决对确定性的追寻。女儿到底为什么自杀,舞台上的女人到底是女人自己还是女儿还是第三者,一场戏结束后,故事会跳到时间在线的哪个地方,答案都不清晰。但正是这种不清晰令《旷野》高度符号化且具有开放性,令人搁置对某一独立确定通路的追求,接受人生就是旷野,哪里都是出路,但哪里都雾气蒙蒙,无边无际。
作者简介
何其乐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就读香港大学文学及文化研究硕士课程。曾参与改编《风尘里》、《女刑警队长》等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以及上海静安戏剧谷、上海国际喜剧节的策划工作,长期为剧情类自媒体账号供稿。创作舞台剧剧本《洞》及《恨逝》。
二月:人生海海
《在一缸大海中活着》的「如水」「风筝计划」二月 公开演读《在一缸大海中活着》纪录文章
「风筝计划」二月 公开演读《在一缸大海中活着》纪录文章
本地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在小说《酒徒》中写下:「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而于《在一缸大海中活着》中,回忆、念想和欲望不只是雾气和水珠,更似是一袭汹涌的波涛及强力的暗涌,将角色和观众都淹没和束缚于本地人的困顿之中。
剧中有三位「人物」:年将三十岁,为前程和家人惆怅的斌仔;刚满十八岁,孩时流离失所,患有恐慌症的凯婷;以及疑似有囤积症,其实是大脑患有疾病的阿梅。此剧开首是写实的:凯婷到男朋友斌仔所居住的公屋单位中密会时,斌仔母亲阿梅从垃圾房抬来她的战利品——一台大型雪柜。雪柜却不慎被卡在大门前,将三人困于堆满杂物的空间之中。情侣之间的调情,母子之间的针锋相对,疑似未来婆媳首次见面的尴尬都使人津津乐道。
但随着第二场开始,鱼缸中的金鱼们展开交流,各角色又在不同时段沉睡和失眠,构成不同组合挖掘回忆及内心情感,对话更具哲学性、内容变得概念化。人物的交流透露出编剧对「爱欲生死」的见解及探索。对于「爱欲」,编剧将亲情、爱情和友情隐含于大大小小的争执和冲突之中,同时亦明确表达出欲望在人生困顿之下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于「生死」,这是个庞大而困难的议题,编剧透过金鱼和人物的思辨,将「人何以为生存」、「我们正在『生存』还是在『死亡』」等问题直接端到观众面前,引人反思自己的生活。
直到剧本结尾,角色面对的回忆及情感正式化作源源不绝的水,直接从雪柜倾泻而出,最终将整个场景都浸没。角色的无奈及无力,透过一片浊水渲染笔者的思绪,即使在风干过后仍留有痕迹,挥之不去。由此可见,即使编剧舍易取难,放下便利大众理解的情节发展,执起象征及比喻作为工具,依然能为人物雕琢出清晰而深刻的生活状态。
虽然编剧的写作意念及风格鲜明清晰,但笔者仍对剧中两个部份感到困惑,望能了解更多作者在选择目前剧情及角色行动时的思路和原因:
一,故事完结于雪柜涌出洪水,将斌仔淹没。斌仔的困局,以及引来的焦躁、烦厌及愤恨,皆源自于抛妻弃子的爸爸、固执己见同时拖累自身的妈妈,以及过往做「错」决定的自己。比起阿梅从外面不知哪里抬回家的雪柜,会否有其他更好的水源,以表现这些负面情绪皆来自斌仔自身的执念?
二,斌仔及阿梅被困于这个「家」之中,当局者迷,所以笔者明白他们因无力而无意打破僵局的决定。但这家的局外人——凯婷呢?她又为何选择与斌仔一起浸沉在水底?作为于这清晨了解这个家的旁观者,作为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年青人,她会否尚有一息生气、一丝动力去带领二人走出这个充斥着污水的家?毕竟求生是每个人的本能,编剧需要用更多笔墨、以更大力度说服观众,令观众认同凯婷选择「潜到水底」的决定是无可避免的。
野生动物纪录片多透过观察动物捕猎和繁殖以显示牠们的生命力,而戏剧则透过刻划人类的选择及行动展现人性。不论是着重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又抑或采用具哲学性的辩证,观众都是通过剧中角色的行动摸索他们的动机,继而推敲出编剧对人生的见解。当然,采取「不行动」和「躺平」亦是一种行动,甚至更能反映出人的某种生存状态,但在经历过一场海啸过后,在颓垣败瓦前放肆完情感,裹足不前并非所有人唯一的选择。角色需要的是甚么?观众想感受到的是甚么?也许是举步前行的勇气及力量。
刁时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现职本地教育工作者,同时就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课程,主修编剧。过往编剧作品包括新域剧团(「剧场里的卧虎与藏龙」)《活寡》、《血肉之躯》;影话戏《暮逸邨谋杀案》、《在家人》,现亦正参与第八届青年编剧剧本写作计划,新作将于五月发表。
剧中有三位「人物」:年将三十岁,为前程和家人惆怅的斌仔;刚满十八岁,孩时流离失所,患有恐慌症的凯婷;以及疑似有囤积症,其实是大脑患有疾病的阿梅。此剧开首是写实的:凯婷到男朋友斌仔所居住的公屋单位中密会时,斌仔母亲阿梅从垃圾房抬来她的战利品——一台大型雪柜。雪柜却不慎被卡在大门前,将三人困于堆满杂物的空间之中。情侣之间的调情,母子之间的针锋相对,疑似未来婆媳首次见面的尴尬都使人津津乐道。
但随着第二场开始,鱼缸中的金鱼们展开交流,各角色又在不同时段沉睡和失眠,构成不同组合挖掘回忆及内心情感,对话更具哲学性、内容变得概念化。人物的交流透露出编剧对「爱欲生死」的见解及探索。对于「爱欲」,编剧将亲情、爱情和友情隐含于大大小小的争执和冲突之中,同时亦明确表达出欲望在人生困顿之下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于「生死」,这是个庞大而困难的议题,编剧透过金鱼和人物的思辨,将「人何以为生存」、「我们正在『生存』还是在『死亡』」等问题直接端到观众面前,引人反思自己的生活。
直到剧本结尾,角色面对的回忆及情感正式化作源源不绝的水,直接从雪柜倾泻而出,最终将整个场景都浸没。角色的无奈及无力,透过一片浊水渲染笔者的思绪,即使在风干过后仍留有痕迹,挥之不去。由此可见,即使编剧舍易取难,放下便利大众理解的情节发展,执起象征及比喻作为工具,依然能为人物雕琢出清晰而深刻的生活状态。
虽然编剧的写作意念及风格鲜明清晰,但笔者仍对剧中两个部份感到困惑,望能了解更多作者在选择目前剧情及角色行动时的思路和原因:
一,故事完结于雪柜涌出洪水,将斌仔淹没。斌仔的困局,以及引来的焦躁、烦厌及愤恨,皆源自于抛妻弃子的爸爸、固执己见同时拖累自身的妈妈,以及过往做「错」决定的自己。比起阿梅从外面不知哪里抬回家的雪柜,会否有其他更好的水源,以表现这些负面情绪皆来自斌仔自身的执念?
二,斌仔及阿梅被困于这个「家」之中,当局者迷,所以笔者明白他们因无力而无意打破僵局的决定。但这家的局外人——凯婷呢?她又为何选择与斌仔一起浸沉在水底?作为于这清晨了解这个家的旁观者,作为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年青人,她会否尚有一息生气、一丝动力去带领二人走出这个充斥着污水的家?毕竟求生是每个人的本能,编剧需要用更多笔墨、以更大力度说服观众,令观众认同凯婷选择「潜到水底」的决定是无可避免的。
野生动物纪录片多透过观察动物捕猎和繁殖以显示牠们的生命力,而戏剧则透过刻划人类的选择及行动展现人性。不论是着重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又抑或采用具哲学性的辩证,观众都是通过剧中角色的行动摸索他们的动机,继而推敲出编剧对人生的见解。当然,采取「不行动」和「躺平」亦是一种行动,甚至更能反映出人的某种生存状态,但在经历过一场海啸过后,在颓垣败瓦前放肆完情感,裹足不前并非所有人唯一的选择。角色需要的是甚么?观众想感受到的是甚么?也许是举步前行的勇气及力量。
作者简介
刁时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现职本地教育工作者,同时就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课程,主修编剧。过往编剧作品包括新域剧团(「剧场里的卧虎与藏龙」)《活寡》、《血肉之躯》;影话戏《暮逸邨谋杀案》、《在家人》,现亦正参与第八届青年编剧剧本写作计划,新作将于五月发表。
《逐流》:与徐波分离后的荒诞「风筝计划」二月 公开演读《逐流》纪录文章
「风筝计划」二月 公开演读《逐流》纪录文章
这不是传统推理戏剧。X3
主角徐波在整个剧本里,对自己杀人的事只说了一个「好」字,没有解释更没有辩护,编剧知道观众求知若渴,就给了几个角色来侧写主角的平凡世界。
妈妈,她眼中的徐波只是一个「叮当百宝袋」,为了生活得更好,一切所需也在他那里予取予携,甚至儿子抽了居屋想成家立室,她脑里想起的画面只是如何与小儿子瓜分徐波的新居,这对她而言是如此合理而平凡。
阿宝,她没有说出和徐波十三年的爱情是怎样过的,但当怀有身孕就立即和他断绝一切关系,既平凡又合理地说明她不能够和徐波有任何将来。
Matthew,徐波的同事。徐波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脱节为他带来很大麻烦,讨厌为自己带来负累。疏远不同频道的人,在职场既平凡又常见。
但这真的只是平凡吗?
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的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文译名的重点是「恶的平凡」。书中的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手上沾满数以万计犹太人的血,但他想着的只是如何令生活过得更好,如何升职讨好上司,因可以「掹衫尾」进入举行「万湖会议」[1]的别墅而沾沾自喜,那怕根本没有任何高层记得他曾站在场地的墙角。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份平凡的工作,过平凡的人生,就如当时大部份的德国人一样,也如同剧中的角色一样,但他们「同构型」地摧毁着别人的人生,徐波只是和社会的标准不同,只是与社会接不上轨,就被社会肆意平凡地压榨,编剧要给观众的不是杀人的理由,而是叩问何以恶是如此平凡。
当观众仍锲而不舍追问杀人原因,编剧到了最后仍只给出一个徐波的梦,反问了一句「原因真的如此重要吗?」在现代宗教失效,人类以为一切也可以用理性去解释的时代,人追求凡事总要有个明确的原因,但这习性是低估了人性的复杂,在「蝴蝶效应」下,每个小小的动作也会如核子反应般一发不可收拾,追寻只是徒然,人生本来就是充满随机性,这是编剧对于人生的见解。但追寻是人性,没有原因的行为是人性,而徐波失望的迭加,对未来想象的幻灭,无法融入世界的彷徨,更加是有血有肉的人性,编剧关心的不是徐波杀人的原因,而是关怀徐波这个「人」。
这个「人」,正在反抗现实。
剧作The Maids的作者尚.惹内(Jean Genet),出生于一个法国的单亲家庭,童年由儿童救济机构照顾,这在当时是平凡而常见,但惹内就是无法接受被安排的人生,以及社会的价值规范。他视自己为社会的局外人,虽自小已显示自己的天赋,但就是不断的盗窃、使用假证件、流浪、做出猥亵行为,一切当时社会视为罪恶的,视为自毁的行径,也被惹内视为反抗社会的工具。同样身为社会局外人的徐波,也以自己的方式——自毁,来反抗这个压榨他的社会。
而自毁的结果,却为他带来了自我救赎。在最后一场,徐波与妈妈在监仓内对话,徐波说「妈,我好钟意呢度。我有独立房㗎,我钟意做咩都得」,他耗尽心力也无法在「自由」社会中求得容身之地,但自毁后却在「受困」的监仓内得到自己的世界,「自由」与「受困」如何定义?编剧继续丢下重磅炸弹。
邪恶如此平凡,人生没有答案,自毁带来救赎,自由源自受困,这一切看似荒谬,但人生本是如此。编剧逼观众直面人生的荒谬,给予的课题相当沉重,虽然剧本仍有很多可进步的空间,但编剧的视野更加珍贵。
[1] 纳粹德国官员为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召开的会议,会议期间落实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何家恒
毕业于浸会大学中国研究课程,现正修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课程,主修编剧。
2016年凭剧本《密室》获得影话戏「第五届青年编剧剧本写作计划」优异奖、影话戏《一丝不挂》及《Dear,佛系YouTuber》联合编剧、凭《龟壳,死鱼,破地狱》入围新域剧团「剧场里的卧虎与藏龙XVI」,并参加影话戏「网上读剧系列」。
主角徐波在整个剧本里,对自己杀人的事只说了一个「好」字,没有解释更没有辩护,编剧知道观众求知若渴,就给了几个角色来侧写主角的平凡世界。
妈妈,她眼中的徐波只是一个「叮当百宝袋」,为了生活得更好,一切所需也在他那里予取予携,甚至儿子抽了居屋想成家立室,她脑里想起的画面只是如何与小儿子瓜分徐波的新居,这对她而言是如此合理而平凡。
阿宝,她没有说出和徐波十三年的爱情是怎样过的,但当怀有身孕就立即和他断绝一切关系,既平凡又合理地说明她不能够和徐波有任何将来。
Matthew,徐波的同事。徐波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脱节为他带来很大麻烦,讨厌为自己带来负累。疏远不同频道的人,在职场既平凡又常见。
但这真的只是平凡吗?
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的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文译名的重点是「恶的平凡」。书中的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手上沾满数以万计犹太人的血,但他想着的只是如何令生活过得更好,如何升职讨好上司,因可以「掹衫尾」进入举行「万湖会议」[1]的别墅而沾沾自喜,那怕根本没有任何高层记得他曾站在场地的墙角。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份平凡的工作,过平凡的人生,就如当时大部份的德国人一样,也如同剧中的角色一样,但他们「同构型」地摧毁着别人的人生,徐波只是和社会的标准不同,只是与社会接不上轨,就被社会肆意平凡地压榨,编剧要给观众的不是杀人的理由,而是叩问何以恶是如此平凡。
当观众仍锲而不舍追问杀人原因,编剧到了最后仍只给出一个徐波的梦,反问了一句「原因真的如此重要吗?」在现代宗教失效,人类以为一切也可以用理性去解释的时代,人追求凡事总要有个明确的原因,但这习性是低估了人性的复杂,在「蝴蝶效应」下,每个小小的动作也会如核子反应般一发不可收拾,追寻只是徒然,人生本来就是充满随机性,这是编剧对于人生的见解。但追寻是人性,没有原因的行为是人性,而徐波失望的迭加,对未来想象的幻灭,无法融入世界的彷徨,更加是有血有肉的人性,编剧关心的不是徐波杀人的原因,而是关怀徐波这个「人」。
这个「人」,正在反抗现实。
剧作The Maids的作者尚.惹内(Jean Genet),出生于一个法国的单亲家庭,童年由儿童救济机构照顾,这在当时是平凡而常见,但惹内就是无法接受被安排的人生,以及社会的价值规范。他视自己为社会的局外人,虽自小已显示自己的天赋,但就是不断的盗窃、使用假证件、流浪、做出猥亵行为,一切当时社会视为罪恶的,视为自毁的行径,也被惹内视为反抗社会的工具。同样身为社会局外人的徐波,也以自己的方式——自毁,来反抗这个压榨他的社会。
而自毁的结果,却为他带来了自我救赎。在最后一场,徐波与妈妈在监仓内对话,徐波说「妈,我好钟意呢度。我有独立房㗎,我钟意做咩都得」,他耗尽心力也无法在「自由」社会中求得容身之地,但自毁后却在「受困」的监仓内得到自己的世界,「自由」与「受困」如何定义?编剧继续丢下重磅炸弹。
邪恶如此平凡,人生没有答案,自毁带来救赎,自由源自受困,这一切看似荒谬,但人生本是如此。编剧逼观众直面人生的荒谬,给予的课题相当沉重,虽然剧本仍有很多可进步的空间,但编剧的视野更加珍贵。
[1] 纳粹德国官员为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召开的会议,会议期间落实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作者简介
何家恒
毕业于浸会大学中国研究课程,现正修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课程,主修编剧。
2016年凭剧本《密室》获得影话戏「第五届青年编剧剧本写作计划」优异奖、影话戏《一丝不挂》及《Dear,佛系YouTuber》联合编剧、凭《龟壳,死鱼,破地狱》入围新域剧团「剧场里的卧虎与藏龙XVI」,并参加影话戏「网上读剧系列」。
生与死的边缘 — 《冰晶儿民》「风筝计划」二月 公开演读《冰晶儿民》纪录文章
「风筝计划」二月 公开演读《冰晶儿民》纪录文章
金鱼被-196 ℃的液态氮迅速冷冻,解冻后又成功复生。这是本剧最先呈现给我们的画面。鱼可复生,人是否亦可?《冰晶儿民》以冷冻技术为切入点,叩问科技与生命的边界。在这个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如何面对生死的抉择?生命的意义是否会有新的变化?
本剧讲了一对夫妻将自己年仅4岁、患脑癌的女儿Einz冷冻的故事。第一幕中采用双线叙事,一条线是从2013年Einz生病之前开始讲述,冷冻前,父母因在冷冻女儿与否的决定上产生分歧。另一条则是2018年Einz被冷冻后,她的哥哥Matrix短暂出家,在寺庙与住持聊天,了解到有关泰国和寺庙所处的地区清迈,也就是金三角的历史。两条线以佛教产生联系,泰国是大多数国民信仰佛教的国家,而佛教的生死观和通俗社会不完全一样,所以在成功冷冻妹妹之后,Matrix一家受到了社会以及民众的舆论攻击。第二幕时间线从2015年顺序行进,Matrix因舆论攻撃感到困惑入庙修行,之后从天才科学家Robert处了解到妹妹复生概率低微。
在冷冻复生这种现代特殊情况下,生命的意义显得尤为迷离,在面对生命逝去的时刻,是释然放手,还是用一丝哪怕非常渺茫的希望去做最后的尝试?这是生活在泰国的科学家家庭的艰难抉择。科技发展飞速,然而科技接触到的未知边缘也愈来愈多。冷冻、复生、意识上传,数字生命,这些词语在新闻中不算陌生,但当自己或家人的生命要经由这些技术来保存时,我们将如何应对?经由这些技术保存的生命,是以怎样的状态存活,甚至是不是存活,都是未知状态。更别说,这样的生命还是不是之前的生命,这又涉及到生命的本质,即剧中多次提到的「『我』是谁」的问题。这些有关生命和自我的讨论经久不衰,在新的现实语境下又有新的发展。新技术对人类的心理和生活的影响是甚么?在新技术之下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
此外,在这部剧开头就引入了很多物理上的概念,这是很有新意的一点。譬如熵,一个热力学中衡量混乱度的指标。热力学上认为在孤立系统中,体系与环境没有能量交换,体系总是自发地向混乱度增大的方向变化,使整个系统的熵值增大。也就是说,如果把整个宇宙看作一个孤立系统,那么它总是朝熵增,也就是更无序的方向变化,如果宇宙终将归于热寂[1],所有的执念是否都没有意义?编剧有提到想借助冷冻这一动作来讨论时间的凝结,当粒子停止运动时,当妹妹处于冷冻时,时间是否仍悄然流逝?
住持以鲤鱼与鱼塘隐喻泰国局势,鲤鱼或象征挣扎的民众,鱼塘则暗指动荡的社会。一家人遭受的攻击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立场有关,而这些人民之间的相互攻击往往是更高一层的大手在拨弄,正如人生在世,所有的遭遇彷佛也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拨弄,而这只手叫做命运,即使是个人的努力和目前的科学,有时也无法左右它。最终,Matrix一家继续向前生活,能看到编剧想告诉我们的,就是用爱去创造自己的人生目的。
[1] 熱寂:宇宙中的有效能量全數轉化為熱能,所有物質溫度達到熱平衡,宇宙中再沒有任何可以維持運動或是生命的能量存在。
袁月洋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就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课程,主修编剧。过往编剧作品包括话剧《一水之遥》(获第二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失去魔法的世界》、《流浪谣》、《我睡了别吵》。
本剧讲了一对夫妻将自己年仅4岁、患脑癌的女儿Einz冷冻的故事。第一幕中采用双线叙事,一条线是从2013年Einz生病之前开始讲述,冷冻前,父母因在冷冻女儿与否的决定上产生分歧。另一条则是2018年Einz被冷冻后,她的哥哥Matrix短暂出家,在寺庙与住持聊天,了解到有关泰国和寺庙所处的地区清迈,也就是金三角的历史。两条线以佛教产生联系,泰国是大多数国民信仰佛教的国家,而佛教的生死观和通俗社会不完全一样,所以在成功冷冻妹妹之后,Matrix一家受到了社会以及民众的舆论攻击。第二幕时间线从2015年顺序行进,Matrix因舆论攻撃感到困惑入庙修行,之后从天才科学家Robert处了解到妹妹复生概率低微。
在冷冻复生这种现代特殊情况下,生命的意义显得尤为迷离,在面对生命逝去的时刻,是释然放手,还是用一丝哪怕非常渺茫的希望去做最后的尝试?这是生活在泰国的科学家家庭的艰难抉择。科技发展飞速,然而科技接触到的未知边缘也愈来愈多。冷冻、复生、意识上传,数字生命,这些词语在新闻中不算陌生,但当自己或家人的生命要经由这些技术来保存时,我们将如何应对?经由这些技术保存的生命,是以怎样的状态存活,甚至是不是存活,都是未知状态。更别说,这样的生命还是不是之前的生命,这又涉及到生命的本质,即剧中多次提到的「『我』是谁」的问题。这些有关生命和自我的讨论经久不衰,在新的现实语境下又有新的发展。新技术对人类的心理和生活的影响是甚么?在新技术之下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
此外,在这部剧开头就引入了很多物理上的概念,这是很有新意的一点。譬如熵,一个热力学中衡量混乱度的指标。热力学上认为在孤立系统中,体系与环境没有能量交换,体系总是自发地向混乱度增大的方向变化,使整个系统的熵值增大。也就是说,如果把整个宇宙看作一个孤立系统,那么它总是朝熵增,也就是更无序的方向变化,如果宇宙终将归于热寂[1],所有的执念是否都没有意义?编剧有提到想借助冷冻这一动作来讨论时间的凝结,当粒子停止运动时,当妹妹处于冷冻时,时间是否仍悄然流逝?
住持以鲤鱼与鱼塘隐喻泰国局势,鲤鱼或象征挣扎的民众,鱼塘则暗指动荡的社会。一家人遭受的攻击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立场有关,而这些人民之间的相互攻击往往是更高一层的大手在拨弄,正如人生在世,所有的遭遇彷佛也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拨弄,而这只手叫做命运,即使是个人的努力和目前的科学,有时也无法左右它。最终,Matrix一家继续向前生活,能看到编剧想告诉我们的,就是用爱去创造自己的人生目的。
[1] 熱寂:宇宙中的有效能量全數轉化為熱能,所有物質溫度達到熱平衡,宇宙中再沒有任何可以維持運動或是生命的能量存在。
作者简介
袁月洋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就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课程,主修编剧。过往编剧作品包括话剧《一水之遥》(获第二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失去魔法的世界》、《流浪谣》、《我睡了别吵》。
三月:夜空中最亮的星
《土星来信》:再等一会。「风筝计划」三月 公开演读《土星来信》纪录文章
「风筝计划」三月 公开演读《土星来信》纪录文章
《土星来信》是一个极其温暖的剧本,暖意抚慰人心。
解开时代下的创伤
故事中两个主人翁虽然在设定上相差六年,但属于同一世代,也正面临生命中不易跨越的狭缝:世俗标准施加无法承受的压力,令生活脱轨。Seven放低专业前景,投身占星;Tim与世隔绝,背负讨厌自己的包袱。
编剧透过Seven为Tim解读星盘的过程,带出《土星》的核心意象:每个人都要经历土星回归;它既是困境,也是磨练;平静面对,心存正念,便能蜕变。故事结尾有两段温柔极致的独白,分别是Tim终于将害死流浪猫的创伤娓娓道来,最后放下包袱,原谅在职场失败的自己;另一段是Seven的来信,既安慰Tim也安慰自己,将土星来袭转化成面对创伤的契机,便可一步一步走过。
笔者认为《土星》的核心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体现出剧场的「解结」能力。可以想象,倘若一个正经历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压力的观众有缘观看此剧,那种温柔、温暖的絮语、耳语,可能便是救起他的关键一手。
故事结构与戏剧行动
故事结构清晰,顺理成章,由Seven占星事业的猎奇案例开始,偶然遇到Tim这位奇怪顾客,再慢慢揭开二人的背景故事,观看时代下小人物的精神面貌。
笔者认为《土星》的高潮并不在于「情节」,而在于「情感」。Tim晕倒是全剧中在「情节」上最大的高潮,它引发后来方小姐的出现,也推动Seven分享自身故事。但笔者认为这个「情节」并非最「紧张」的时刻,此剧最令人「紧张」的,是主人翁能否「透过重述经历来跟自己和解」——角色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瞬间,才是《土星》最扣人心弦之处。
这种独特之处构成此剧特色:故事侧重剖白过去内容,而非解决眼前困境的戏剧行动。《土星》有不少篇幅由角色剖白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些经历细腻动人,捕捉生命中的微妙时刻,深入人性;但这些内容都发生在「过去」,对「当下」的角色而言,最大的影响是他们的性格和能否面对的「决定」。这可能构成一个情况:观众必须对角色的过去有莫大的好奇,才有动力追看故事下去。
丝丝入扣的意象
《土星》意象丰富,充满诗意;意象之间互相呼应,有趣而不突兀;建构具体记忆点,容易回想和回味。
土星回归、扰人的水管声、转化出来的风铃声,和入口酸涩的「幸运糖」,比喻人生不如意事总会渡过(虽然编剧在对白中自嘲「灌鸡汤」,但这种温柔的「灌」法,观众比较受落);那只Tim尝试拯救最后却本末倒置的流浪猫,仿佛便是无法与俗世框架契合的Tim,被冠冕堂皇的社会牺牲。笔者最深刻的,是Seven不知从哪里闻到的臭味;那股可能由自身散发、颓废、被厌恶的气息,充满质感,由文字刺激想象,细腻微妙,而且一针见血。这些意象为《土星》建构一幅丰富的星图。
结语
笔者认为《土星》是一个发自内心、充满热度、处处善意的作品;那股触及心灵深处的力量,正是当下都市人需要的滋养:再等一会,总会过的。期待她会成为一个更加精炼和具备追看性的作品,在剧场里散发温暖的光芒。
李伟乐
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课程,主修编剧(优异)。
凭《尘落无声》提名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剧本,IATC(HK)剧评人奖年度剧本/编剧及香港小剧场奖最佳剧本。
近年编剧作品:香港话剧圑读戏剧场《别来无恙》、文本特区《水中不知流》及「新戏匠」系列《病房》;同流《移家女孩2.0》、《今晚,Omakase夜唔夜?》;剧毒演读剧《苏拉超人与索奇星怪的第794回》及三色豆剧团演读剧场《野战》(联合编剧)。
现职编剧和戏剧导师。
解开时代下的创伤
故事中两个主人翁虽然在设定上相差六年,但属于同一世代,也正面临生命中不易跨越的狭缝:世俗标准施加无法承受的压力,令生活脱轨。Seven放低专业前景,投身占星;Tim与世隔绝,背负讨厌自己的包袱。
编剧透过Seven为Tim解读星盘的过程,带出《土星》的核心意象:每个人都要经历土星回归;它既是困境,也是磨练;平静面对,心存正念,便能蜕变。故事结尾有两段温柔极致的独白,分别是Tim终于将害死流浪猫的创伤娓娓道来,最后放下包袱,原谅在职场失败的自己;另一段是Seven的来信,既安慰Tim也安慰自己,将土星来袭转化成面对创伤的契机,便可一步一步走过。
笔者认为《土星》的核心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体现出剧场的「解结」能力。可以想象,倘若一个正经历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压力的观众有缘观看此剧,那种温柔、温暖的絮语、耳语,可能便是救起他的关键一手。
故事结构与戏剧行动
故事结构清晰,顺理成章,由Seven占星事业的猎奇案例开始,偶然遇到Tim这位奇怪顾客,再慢慢揭开二人的背景故事,观看时代下小人物的精神面貌。
笔者认为《土星》的高潮并不在于「情节」,而在于「情感」。Tim晕倒是全剧中在「情节」上最大的高潮,它引发后来方小姐的出现,也推动Seven分享自身故事。但笔者认为这个「情节」并非最「紧张」的时刻,此剧最令人「紧张」的,是主人翁能否「透过重述经历来跟自己和解」——角色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瞬间,才是《土星》最扣人心弦之处。
这种独特之处构成此剧特色:故事侧重剖白过去内容,而非解决眼前困境的戏剧行动。《土星》有不少篇幅由角色剖白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些经历细腻动人,捕捉生命中的微妙时刻,深入人性;但这些内容都发生在「过去」,对「当下」的角色而言,最大的影响是他们的性格和能否面对的「决定」。这可能构成一个情况:观众必须对角色的过去有莫大的好奇,才有动力追看故事下去。
丝丝入扣的意象
《土星》意象丰富,充满诗意;意象之间互相呼应,有趣而不突兀;建构具体记忆点,容易回想和回味。
土星回归、扰人的水管声、转化出来的风铃声,和入口酸涩的「幸运糖」,比喻人生不如意事总会渡过(虽然编剧在对白中自嘲「灌鸡汤」,但这种温柔的「灌」法,观众比较受落);那只Tim尝试拯救最后却本末倒置的流浪猫,仿佛便是无法与俗世框架契合的Tim,被冠冕堂皇的社会牺牲。笔者最深刻的,是Seven不知从哪里闻到的臭味;那股可能由自身散发、颓废、被厌恶的气息,充满质感,由文字刺激想象,细腻微妙,而且一针见血。这些意象为《土星》建构一幅丰富的星图。
结语
笔者认为《土星》是一个发自内心、充满热度、处处善意的作品;那股触及心灵深处的力量,正是当下都市人需要的滋养:再等一会,总会过的。期待她会成为一个更加精炼和具备追看性的作品,在剧场里散发温暖的光芒。
作者简介
李伟乐
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课程,主修编剧(优异)。
凭《尘落无声》提名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剧本,IATC(HK)剧评人奖年度剧本/编剧及香港小剧场奖最佳剧本。
近年编剧作品:香港话剧圑读戏剧场《别来无恙》、文本特区《水中不知流》及「新戏匠」系列《病房》;同流《移家女孩2.0》、《今晚,Omakase夜唔夜?》;剧毒演读剧《苏拉超人与索奇星怪的第794回》及三色豆剧团演读剧场《野战》(联合编剧)。
现职编剧和戏剧导师。
《刺客与渔女》:从渔女说起「风筝计划」三月 公开演读《土星来信》纪录文章
「风筝计划」三月 公开演读《土星来信》纪录文章
《刺客与渔女》(以下简称《刺》)重新讲述春秋时期刺客专诸的故事。对于大多编剧而言,改编历史故事并不容易。通常观众大多已知晓大致情节,甚至能预判角色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当代观众重新投入,并赋予故事新的生命力,成为改编历史剧的最大挑战。编剧潘惠森曾在《都是龙袍惹的祸》中所言:「时间地点全都交代了,这就是历史……我最想知道的没有告诉我。这也是历史,或叫历史的秘密。」对笔者而言,改编历史剧的核心在于掌握讲故事的秘诀。历史的力量在于它所承载的智慧与经验,但故事能否穿越时空,则取决于讲述者如何将它转化为与观众共鸣的情感与哲理。《刺》的创作灵感来自编剧武庭英对专诸故事中鱼肠剑的「鱼」的追问。历史的书写着重在公子光、伍子胥和专诸身上,世人只知「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1],而不见历史齿轮下的平民百姓、成大事背后的人性挣扎。为了补充这段空白,编剧运用想象力虚构核心角色——渔女姣奴。正是渔女拼命获得那尾最鲜美的鱼,才成就这段流传千古的历史。笔者将简述《刺》的剧本结构,重点梳理「渔女」在整个剧本的作用,以及浅谈剧中叙事策略。
虚构角色的作用:渔女的角色设计
《刺》全剧分成六幕:序幕、第一至四幕、尾声。每一幕围绕底层市民(代表人物:专诸与姣奴)与权贵阶层(代表人物:伍子胥)之间的互动,两方力量彼此交织,共同推动情节发展。
序幕: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尾声:
由此可见,渔女姣奴贯穿整个故事。《刺》的主要情节以线性方式展开,从渔夫之死、姣奴惨遭凌辱、姣奴捕鱼赎身、姣奴之死,逐步推动主角专诸刺杀王僚的行动,也揭示了底层人物的被动性与无力感。姣奴的牺牲使专诸的刺杀动机变得复杂,同时增添故事的情感张力。
剧中多数角色在历史轶事中有迹可寻,例如:专诸惧内[2]、专诸母亲自尽[3]、专诸之子被封为上卿[4]等。更不用说公子光、伍子胥和专诸,他们在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被大量着墨记载,其背后的动机以及当时的局势也被剖析得细致入微。这些数据有助编剧建立每个角色的基调。《刺》的角色形象立体饱满,有血有肉——专诸的痛苦和举步维艰、专诸妻子的聪明、专诸母亲的智慧、伍子胥的仇恨、公子光的口不对心等。而在笔者看来,姣奴的角色相对扁平,其作用更像是推动专诸的事件触发点。渔女姣奴敢爱敢恨、不畏强权、勇于发声,还有她的纯洁都赋予全剧更深层次的隐喻意义。或者应该说,渔女更像是高度理想化的象征。相比之下,刺客专诸的形象则显得更复杂且丰富,尤其是在与母亲交谈时的两段长独白,深刻揭示了「侠客」与「刺客」的区别以及他内心的挣扎。专诸的行动表面上出于「侠义」,但编剧通过对其心理挣扎的描写,将他的行动转化成对命运的抗争与妥协。他的选择并非完全出于自由意志,而更像是一种「身不由己」中的「勇气」抉择,折射出当代个体的困境。
叙事策略:线性与环形
《刺》的叙事结构结合了线性推进与环形叙事。主要情节以线性方式展开,第一至第四幕描写了刺杀王僚行动前三天的关键事件。如上所述,剧情聚焦姣奴的遭遇,层层递进的危机推动专诸走向刺杀王僚的高潮。时间的压缩与情节的递进成功营造强烈的紧迫感,使专诸的每一步选择都显得迫在眉睫,增加追看性,同时突显出专诸的挣扎与「身不由己」。然而,剧本虽成功塑造专诸复杂立体的形象,对伍子胥与公子光一方的刻画却略嫌薄弱,削减了整体叙事的平衡与可信性。剧本有意结合姣奴之死与刺杀王僚的因果关系,并设定王僚要求三天内献鱼,从而限定刺杀行动的准备须在三天内完成。反观历史记载,刺杀行动与楚平王之死密切相关:吴王僚趁楚国国丧发兵攻楚,导致吴军受困,公子光认为时机成熟,遂发动刺杀行动。现时剧本处理虽增加了戏剧张力,却让刺杀行动显得草率鲁莽,既低估了公子光的计谋,同时削弱了专诸作为刺客的重量。笔者欣赏编剧通过虚构角色渔女去重写历史的宏大叙事,增添个体的声音,然而如何还原历史事件中各角色的合理动机是剧本的关键所在。
此外,剧本将灵堂设为序幕与尾声的场景,承载伍子胥与专诸及渔女的鬼魂对话,形成首尾呼应的环形结构。在这样的编排下,主线的线性推动被包裹在环形结构内,带来一种凝滞的氛围。灵堂中的鬼魂对话让笔者联想起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雷特》(Hamlet)和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这两部作品皆改编自历史背景或传说,同样使用鬼魂作为叙事符号。在《哈姆雷特》中,父王鬼魂的出现带来故事的悬念,促使主角哈姆雷特验证父亲之死的真相并展开复仇行动。鬼魂既是推动剧情的诱因,同时是主角心理状态的映射。在《哥本哈根》中,三个鬼魂——尼尔斯.波尔、玛格丽特.波尔以及维尔纳.海森堡——共同回顾海森堡于1941年纳粹占领下的哥本哈根神秘访问,试图从不同视角拼凑出真相。第一幕的台词「现在,我们三个都已死去……现在,没有人会再受到伤害,没有人会再被背叛。」(Now we are all three of us dead and gone...... Now no one can be hurt, now no one can be betrayed.)点出了鬼魂的特殊作用:因为角色已死,他们得以摆脱当时的私欲与偏见,追寻真相的讨论因此更为纯粹。读过《刺》后,笔者反复思索剧中鬼魂的作用可以是甚么?如果删去灵堂这两场戏会影响主题的呈现吗?在序幕中,笔者一度以为伍子胥、专诸与渔女三者势均力敌。随着剧情展开,故事逐渐偏向以专诸的视角推进,姣奴成为推动专诸行动的关键角色,而伍子胥则退居为推手与历史的见证者。笔者思考应该如何理解专诸这位已死的主角?伍子胥在序幕中坦言自己已遗忘眼前这两个亡魂,专诸才会再次讲述那三天的故事。从一人两鬼的对话带出主线情节的安排,似乎加深无力感——专诸与渔女是否被困在往事的记忆中,而对世界没有实质的撼动?为甚么编剧在序幕要通过伍子胥去引入故事,而不是其他角色,例如专诸的儿子?伍子胥的遗忘是有意抹去他们的存在,还是随着时间流逝与复仇的快感而无意淡忘?在尾声中,伍子胥为何能和应亡魂并寄语「能救一个是一个」?这些安排都耐人寻味,值得大家深思。剧本仍在发展阶段,但已展现出深刻的思想与编剧刻画角色的功力,让笔者期待故事后续发展。
[1] 出自《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2] 出自《越绝书》
[3] 出自《东周列国志》
[4] 出自《史记》
侯亦岚
现就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硕士,主修编剧。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中长篇小说入选字花「开故」作家育成计划。近期编剧作品:呼吸劇團《流離之際III—如廁之夢》及蛇口戲劇節新寫作計劃《蛛絲》。
虚构角色的作用:渔女的角色设计
《刺》全剧分成六幕:序幕、第一至四幕、尾声。每一幕围绕底层市民(代表人物:专诸与姣奴)与权贵阶层(代表人物:伍子胥)之间的互动,两方力量彼此交织,共同推动情节发展。
序幕:
- 伍子胥在灵堂上遇见刺客专诸与渔女姣奴的亡魂。
第一幕:
- 渔夫(姣奴之父)因一条鱼而得罪权贵,在菜市中被刺死。
- 伍子胥与公子光去菜市场找专诸。
第二幕:
- 专诸在家中与老母亲、妻子谈论渔夫之死。
- 伍子胥与公子光登门拜访专诸,从渔夫之死过渡到专诸应该杀吴王僚的动机。
第三幕:
- 专诸在菜市场中得知姣奴被俘虏,更惨遭凌辱。
- 伍子胥出谋献策,公子光向吴王僚提出捕捉鲜鱼的条件,交换姣奴三天的人身自由。
第四幕:
- 姣奴向专诸告白,其后为了捕鱼,葬身太湖。
- 专诸带着鲜鱼向伍子胥、公子光复命,其后成功刺杀王僚。
尾声:
- 重回序幕的灵堂,伍子胥终于记起专诸与姣奴。
由此可见,渔女姣奴贯穿整个故事。《刺》的主要情节以线性方式展开,从渔夫之死、姣奴惨遭凌辱、姣奴捕鱼赎身、姣奴之死,逐步推动主角专诸刺杀王僚的行动,也揭示了底层人物的被动性与无力感。姣奴的牺牲使专诸的刺杀动机变得复杂,同时增添故事的情感张力。
剧中多数角色在历史轶事中有迹可寻,例如:专诸惧内[2]、专诸母亲自尽[3]、专诸之子被封为上卿[4]等。更不用说公子光、伍子胥和专诸,他们在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被大量着墨记载,其背后的动机以及当时的局势也被剖析得细致入微。这些数据有助编剧建立每个角色的基调。《刺》的角色形象立体饱满,有血有肉——专诸的痛苦和举步维艰、专诸妻子的聪明、专诸母亲的智慧、伍子胥的仇恨、公子光的口不对心等。而在笔者看来,姣奴的角色相对扁平,其作用更像是推动专诸的事件触发点。渔女姣奴敢爱敢恨、不畏强权、勇于发声,还有她的纯洁都赋予全剧更深层次的隐喻意义。或者应该说,渔女更像是高度理想化的象征。相比之下,刺客专诸的形象则显得更复杂且丰富,尤其是在与母亲交谈时的两段长独白,深刻揭示了「侠客」与「刺客」的区别以及他内心的挣扎。专诸的行动表面上出于「侠义」,但编剧通过对其心理挣扎的描写,将他的行动转化成对命运的抗争与妥协。他的选择并非完全出于自由意志,而更像是一种「身不由己」中的「勇气」抉择,折射出当代个体的困境。
叙事策略:线性与环形
《刺》的叙事结构结合了线性推进与环形叙事。主要情节以线性方式展开,第一至第四幕描写了刺杀王僚行动前三天的关键事件。如上所述,剧情聚焦姣奴的遭遇,层层递进的危机推动专诸走向刺杀王僚的高潮。时间的压缩与情节的递进成功营造强烈的紧迫感,使专诸的每一步选择都显得迫在眉睫,增加追看性,同时突显出专诸的挣扎与「身不由己」。然而,剧本虽成功塑造专诸复杂立体的形象,对伍子胥与公子光一方的刻画却略嫌薄弱,削减了整体叙事的平衡与可信性。剧本有意结合姣奴之死与刺杀王僚的因果关系,并设定王僚要求三天内献鱼,从而限定刺杀行动的准备须在三天内完成。反观历史记载,刺杀行动与楚平王之死密切相关:吴王僚趁楚国国丧发兵攻楚,导致吴军受困,公子光认为时机成熟,遂发动刺杀行动。现时剧本处理虽增加了戏剧张力,却让刺杀行动显得草率鲁莽,既低估了公子光的计谋,同时削弱了专诸作为刺客的重量。笔者欣赏编剧通过虚构角色渔女去重写历史的宏大叙事,增添个体的声音,然而如何还原历史事件中各角色的合理动机是剧本的关键所在。
此外,剧本将灵堂设为序幕与尾声的场景,承载伍子胥与专诸及渔女的鬼魂对话,形成首尾呼应的环形结构。在这样的编排下,主线的线性推动被包裹在环形结构内,带来一种凝滞的氛围。灵堂中的鬼魂对话让笔者联想起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雷特》(Hamlet)和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这两部作品皆改编自历史背景或传说,同样使用鬼魂作为叙事符号。在《哈姆雷特》中,父王鬼魂的出现带来故事的悬念,促使主角哈姆雷特验证父亲之死的真相并展开复仇行动。鬼魂既是推动剧情的诱因,同时是主角心理状态的映射。在《哥本哈根》中,三个鬼魂——尼尔斯.波尔、玛格丽特.波尔以及维尔纳.海森堡——共同回顾海森堡于1941年纳粹占领下的哥本哈根神秘访问,试图从不同视角拼凑出真相。第一幕的台词「现在,我们三个都已死去……现在,没有人会再受到伤害,没有人会再被背叛。」(Now we are all three of us dead and gone...... Now no one can be hurt, now no one can be betrayed.)点出了鬼魂的特殊作用:因为角色已死,他们得以摆脱当时的私欲与偏见,追寻真相的讨论因此更为纯粹。读过《刺》后,笔者反复思索剧中鬼魂的作用可以是甚么?如果删去灵堂这两场戏会影响主题的呈现吗?在序幕中,笔者一度以为伍子胥、专诸与渔女三者势均力敌。随着剧情展开,故事逐渐偏向以专诸的视角推进,姣奴成为推动专诸行动的关键角色,而伍子胥则退居为推手与历史的见证者。笔者思考应该如何理解专诸这位已死的主角?伍子胥在序幕中坦言自己已遗忘眼前这两个亡魂,专诸才会再次讲述那三天的故事。从一人两鬼的对话带出主线情节的安排,似乎加深无力感——专诸与渔女是否被困在往事的记忆中,而对世界没有实质的撼动?为甚么编剧在序幕要通过伍子胥去引入故事,而不是其他角色,例如专诸的儿子?伍子胥的遗忘是有意抹去他们的存在,还是随着时间流逝与复仇的快感而无意淡忘?在尾声中,伍子胥为何能和应亡魂并寄语「能救一个是一个」?这些安排都耐人寻味,值得大家深思。剧本仍在发展阶段,但已展现出深刻的思想与编剧刻画角色的功力,让笔者期待故事后续发展。
[1] 出自《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2] 出自《越绝书》
[3] 出自《东周列国志》
[4] 出自《史记》
作者简介
侯亦岚
现就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硕士,主修编剧。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中长篇小说入选字花「开故」作家育成计划。近期编剧作品:呼吸劇團《流離之際III—如廁之夢》及蛇口戲劇節新寫作計劃《蛛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