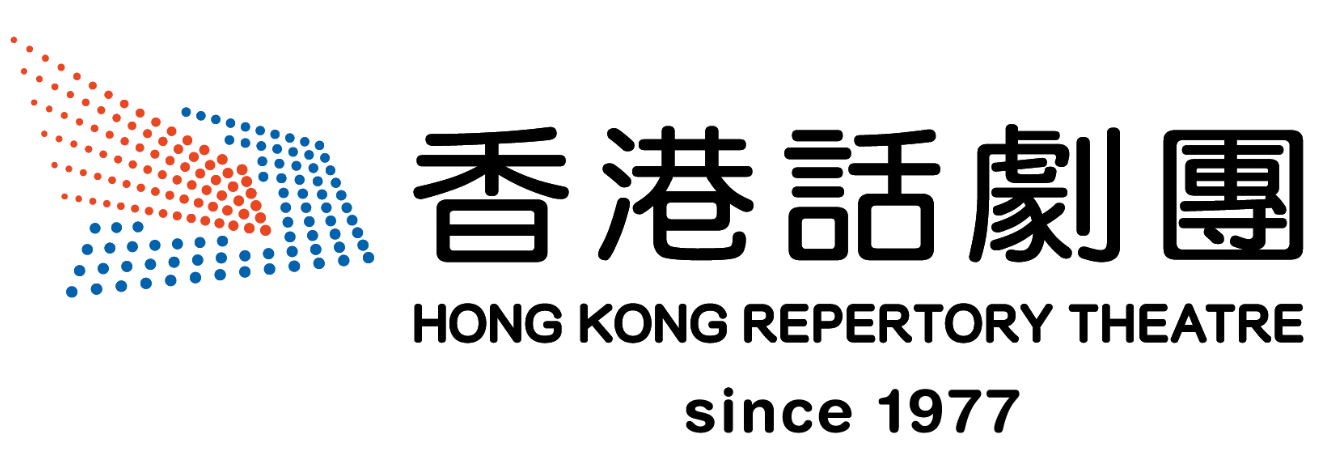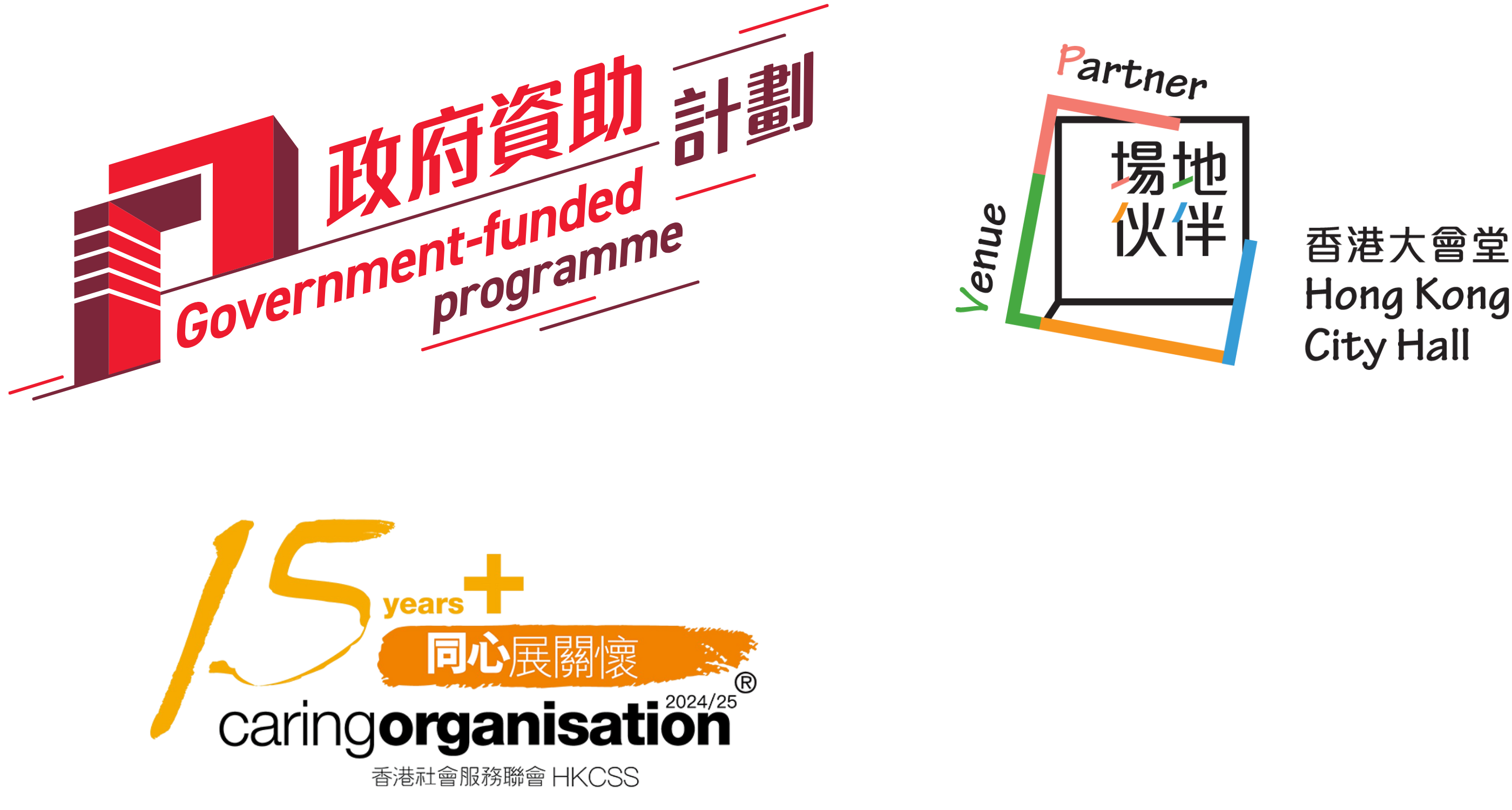戲劇文學
陌生的自我及其文化隱喻—對《往大馬士革之路》的一種解讀
1886年,奧古斯特.史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自傳《一個女僕的兒子》(The Son of the Servant)。在一次訪談中,他說:「我認為,完整地描述一個人的一生要比完整地描述一個家庭真實和有啟發得多……人們只瞭解一種人生,他自己的……」隨後,他又接連出版了《一個愚人的自白》(The Confession of a Fool, 1893)、《地獄》(Inferno, 1897) 等書。據專家考證,這些著作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自傳,因為書中雖有大量真實的細節,卻又夾雜著太多的想像、夢幻和編造……書中那位名叫史特林堡的主人公,其實是一個混雜著真實和虛構的綜合體;那個不斷出現在他的系列作品中既是犧牲品、又是救世主的「陌生人」,與傳主不是同一個人。
史特林堡的主要劇作,從早期的《父親》(The Father, 1887),中期的《往大馬士革之路》三部曲 (To Damascus: Parts 1-3, 1898–1901)、《一齣夢的戲劇》(A Dream Play, 1901),到後期的《大路》(The Great Highway, 1909)……其主人公大體也屬於這一類型。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如夢如幻,詭異荒忽,隱秘的心靈活動變成直觀呈現的戲劇「場景」,紛紛遝遝,莫可窮詰。作為從傳統戲劇掙脫出來的激進的先鋒作品,作為傳遞新思潮、新觀念的現代戲劇的起點,這些作品自有其內在的真實性和不朽的藝術價值。彼得.斯叢狄 (Peter Szondi) 在《現代戲劇理論》(Theory of the Modern Drama) 一書中,將這種戲劇樣式稱為「場景劇」(Stationendrama)。
「場景劇」一反傳統戲劇、尤其是佳構劇環環緊扣的情節結構,不倚重因果關聯的時空順序,更沒有由矛盾衝突所推動的連續性情節,而是由圍繞一個中心人物所鋪陳的一系列鬆散的戲劇場景所構成。場景劇也可以說是一種主觀戲劇。它從中心人物的主觀視角觀察周圍世界及其自身,描述中心人物內在(精神)的發展道路,揭示中心人物隱秘的心靈活動,以自我的統一取代情節的統一。
在《往大馬士革之路》中,主人公陌生男,無名無姓,生活在超歷史時空中。他是該隱(Cain,額頭有被刀斧砍傷的明顯記號)[1];他是雅各(Jacob,走路一瘸一拐)[2];他是乞丐、是瘋子、是凱撒……在他身上彙集了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特徵,可以說,他是一個不同的人的複合體。或者說,他是史特林堡心目中的人類的象徵。
陌生男忤時憤世,孤行獨市,內心騷動不安,飄繚搖盪,從深度壓抑到無端喜樂,情緒起伏不定,有如精神分裂症病患的極度敏感與狂熱暴烈。一方面,他抱怨自己是一個被社會碾壓與拋棄的人,一個多餘人、局外人、陌生人;另一方面,又自視甚高,把自己看成是這個世界生存的最後救贖。
劇中出現的其他人:醫生、乞丐、瘋子、凱撒,甚至婦人……都可以說是陌生男這一中心人物的自我投射。然而,這些斷裂成無數碎片的「自我」,也不再是陌生男所熟悉的「自我」。當外射的自我變成自我意識審視的他者時,已完全異化成某種讓人難以辨識的東西。也就是說,陌生男在各個場景中遇到的人與事,包括醫生、乞丐、瘋子、凱撒、婦人……既是陌生男的自我,又不完全是陌生男的自我;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自我返回自身,從無意識的自我,變成意識到的自我,是一個充滿悖論的過程。一如彼得.斯叢狄所指出的,個體的自我與異化—對象化世界的對立,構成了史特林堡許多作品形式結構的基礎。
在《地獄》一書中,史特林堡寫道:「從孩提時代起,我就開始尋找上帝,而我發現的卻是魔鬼。」一方面,他從不停止痛斥現實的污垢與生存的錯亂;一方面又不懈地呼喊要匡正這個脫節的世界。這從全劇的劇名、劇作結構等諸多方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
劇名中的「大馬士革」,只有模糊不清的宗教意義。生活在別處,大馬士革無論是象徵聖地或人間樂園,都虛懸在主人公的旅程之外。
陌生男千里投荒的流浪旅程(或心路歷程),從第一場的「大街轉角」,回到最後一場的「大街轉角」,兜了一大圈,終點回到起點,沒有歷史,只有重複。
史特林堡一生遭受精神分裂症的多次困擾。然而,難能可貴的是他將這種傷害轉化成深刻的人生體驗與對世界的領悟,並在一系列戲劇作品中,以獨到的場景劇的形式將其呈現出來。無論這種呈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或背離精神分裂症的內在真實,也無論那種難以言明的神秘能否言說,它都幫助我們了悟藝術與生命所潛含的形而上學或宗教上的意義。
德國哲學家、精神病理專家卡爾.雅斯貝斯 (Karl Jaspers) 稱史特林堡為「客觀表現性的精神分裂症藝術家」,認為精神分裂症的病情發作,誘發了史特林堡原初人格中既有的藝術天賦。這涉及醫學上更為精專的病理學問題。毫無疑問,並不是凡有藝術天賦的精神分裂症病患都能成為藝術家。我認為,在生存的掙扎與對抗,在對藝術的不斷探索與追問中,敞開生存與人性的深淵,從而達到生命體驗罕見的深度與另一個思維層次,或許才是史特林堡一類藝術家獲得崇高藝術成就更重要的原因。
史特林堡對於我們之所以重要,不在於他的作品或許可以被當作扭曲了的精神分裂症的藝術案例,而是在文化意義上,喚醒世人反省時代整體的精神處境,以及歷史目的化過程喪失給人類所帶來的精神困境。雅斯貝斯將精神分裂症看成是西方現代文化頹敗的隱喻。他說:「今天的問題可以從以下事實中找到答案:我們生活的根基已被動搖。時代問題敦促我們反省終極的問題與即刻體驗。」(見《史特林堡與梵高》[3] 一書)事實上,資本與權力的雙重壓迫,整體文化與生存處境正在經歷急劇的變化。變得陌生的不僅是客觀世界,還有你自己。
西方如此,東方如此,香港亦如此。
[1] 編按:《聖經‧創世紀》中亞當和夏娃所生之子。該隱出於妒意殺了弟弟亞伯後,神在其額頭作了記號。
[1] 編按:《聖經‧創世紀》中亞當和夏娃所生之子。該隱出於妒意殺了弟弟亞伯後,神在其額頭作了記號。
[2] 編按:《聖經‧創世紀》中出現的人物。雅各與神摔跤時扭傷大腿,被改名為以色列。
[3] Strindberg and Van Gogh: an attempt of a pathographic analysis with reference to parallel cases of Swedenborg and Hold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