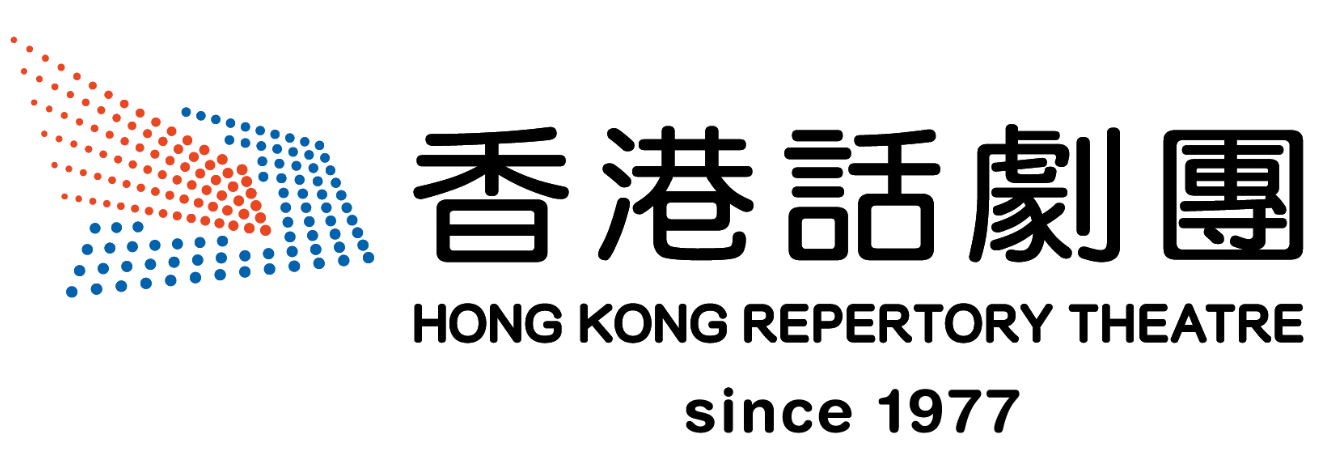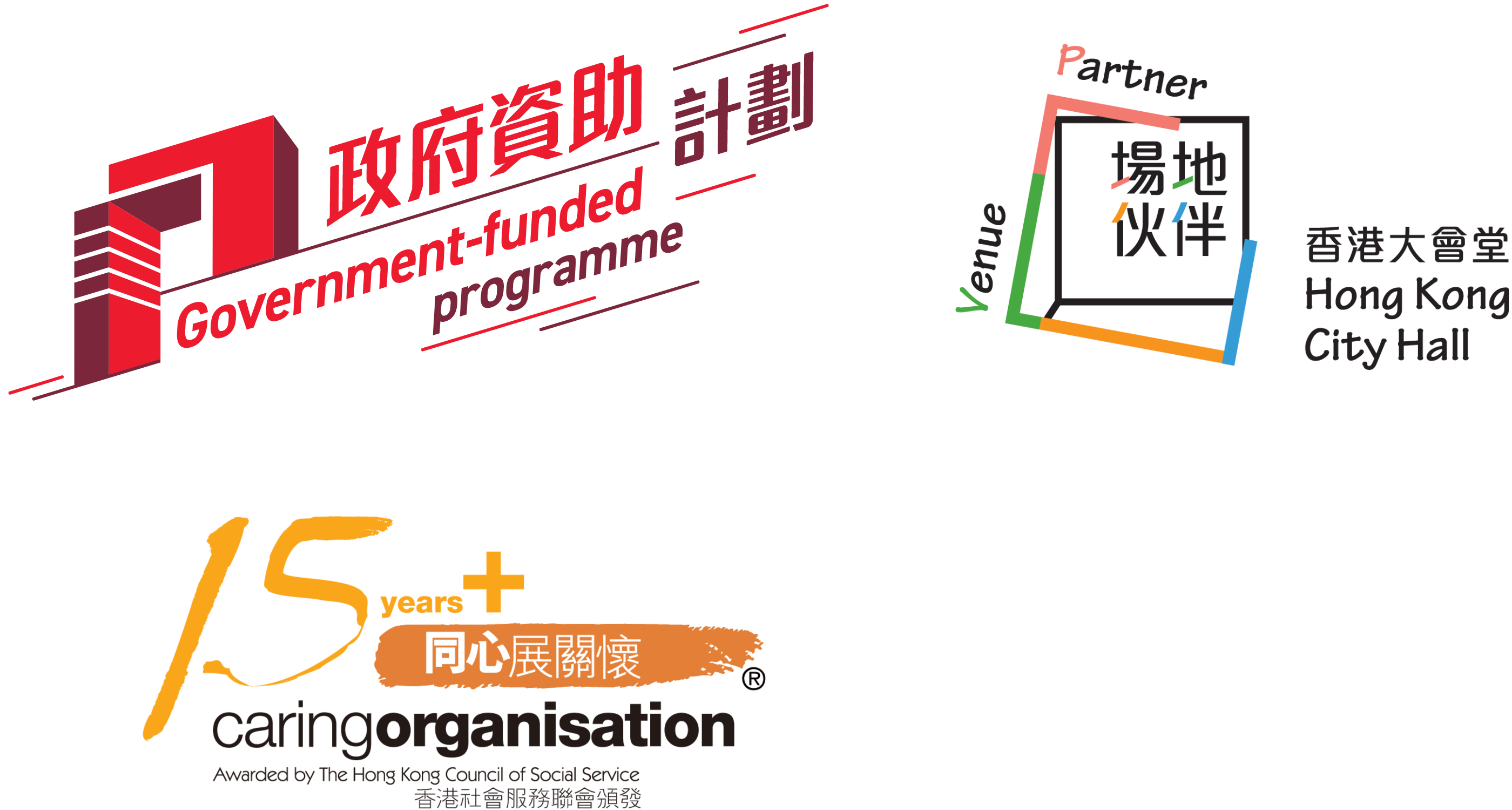戲劇文學
「重新」創作︰《塘西馴悍記》「之前與之後」講座紀錄文章
重新創作。人活著的每一天,或許都是一次「重新」創作,只是有些事件、經歷以及選擇比較重大,以至在人生上加了「之前與之後」的刻度。例如,「之前」是一個劇團的藝術總監,「之後」是一間戲劇學院的老師;「之前」是一間戲劇學院的院長,「之後」是一個全職劇團的藝術總監,好像生活突然拐了一個彎。說的是稍前藝術總監潘Sir到演藝學院,跟學生以題目「之前與之後」分享創作《塘西馴悍記》的經歷。
之前,「重新」創作又被稱為「重創」,但不是因為「重大創傷」,而是源由自歐洲中世紀的一個英文詞語。當時書寫的材料多以動物的皮製成,例如羊皮紙,因為羊皮紙非常珍貴,所以是會重用的,方法就是把上面的文字「刮掉」,然後再重新書寫,形容這個過程的英文詞語Palimpsest,潘Sir將之稱為「重創」。每一個故事總是被寫完又寫,無論是莎士比亞的《馴悍記》,還是巷弄之間的一次偶遇,都會在口耳相傳之間,「重創」又「重創」。故事由多種風格交織而成就,又在交織間延展更多的意義,和意義的共振。
之後,創作屬於當下,「重創」、改寫、延續屬於當下的事。然而這個當下,可以包含著過去、現在與未來,莎士比亞也寫過很多包含歷史人物的劇作,所有「之前」與「之後」也是共時的。時代錯置(Anachronism)是一種文學手法,把不可能出現在同一時代的人事物並置,而那些人事物包括人物、事件、語言、技術、物質、食物、音樂和藝術風格等等。在創作中,所有時代都可以同時存在,因為在人的故事,人的生活中,人性始終不變。
之前與之後,在它們之間,就是語言的事了。語言填滿時間的空白,有標準化的、政治性的「語言」,也有未標準化的,屬於地方的「方言」。語言與方言,經過編排,形成了節奏,高低起伏如歌的韻律,那是語言的音樂性(Musicality)。在語言之外有了音樂,在音樂之中又有了語言,意義不再是堅硬的石壁,而是其中往外滲的水,似有若無,溫柔地滋潤。
時間有連續性,總是向前累積,重新創作是把說完了又說、古老而經典的故事重新說一遍,人人都有說故事的方法,在羊皮紙上用自己的筆劃疊加累積,前人的痕跡模糊了卻又隱約可見,後人的筆跡又與前人的交錯重疊;每個人,在無限大的創作宇宙中,如何打撈自己閃爍的寶藏?
潘Sir說起另一種藝術形式,雕塑。同樣是經過千錘百煉的敲打,一塊石頭才成為了一尊雕塑。在敲打與挖掘之中想要傳達的是什麼?中式雕塑與西式雕塑大有不同,西式雕塑,講究精緻地模仿人的臉容表情、肌肉線條;中式雕塑,則以相對平面的亞洲人臉容為雕塑對象,探尋是如何傳遞人的精神。畫家陳丹青形容,中式雕塑著重「高度概括」和「去除所有多餘細節」,如同京劇中的臉譜化,或山水畫對意境的捕捉,或古典詩歌的言有盡而意無窮。
改編這回事,「重創」這回事,核心都在於對人性,對精神,對意境的追求,在情節之內,語言之外,挖掘埋藏在不同創作之中的人性寶藏。無論哪一個時代,在故事與歷史之中,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所有「人」都走在同一條路上。之前與之後的拐點,若離開道路遠一點去看,彎路看來也像一條直路,而再離得遠一點去看,又或許生命是一個圓,每次拐彎都向著起點更靠近一點。
之前,「重新」創作又被稱為「重創」,但不是因為「重大創傷」,而是源由自歐洲中世紀的一個英文詞語。當時書寫的材料多以動物的皮製成,例如羊皮紙,因為羊皮紙非常珍貴,所以是會重用的,方法就是把上面的文字「刮掉」,然後再重新書寫,形容這個過程的英文詞語Palimpsest,潘Sir將之稱為「重創」。每一個故事總是被寫完又寫,無論是莎士比亞的《馴悍記》,還是巷弄之間的一次偶遇,都會在口耳相傳之間,「重創」又「重創」。故事由多種風格交織而成就,又在交織間延展更多的意義,和意義的共振。
之後,創作屬於當下,「重創」、改寫、延續屬於當下的事。然而這個當下,可以包含著過去、現在與未來,莎士比亞也寫過很多包含歷史人物的劇作,所有「之前」與「之後」也是共時的。時代錯置(Anachronism)是一種文學手法,把不可能出現在同一時代的人事物並置,而那些人事物包括人物、事件、語言、技術、物質、食物、音樂和藝術風格等等。在創作中,所有時代都可以同時存在,因為在人的故事,人的生活中,人性始終不變。
之前與之後,在它們之間,就是語言的事了。語言填滿時間的空白,有標準化的、政治性的「語言」,也有未標準化的,屬於地方的「方言」。語言與方言,經過編排,形成了節奏,高低起伏如歌的韻律,那是語言的音樂性(Musicality)。在語言之外有了音樂,在音樂之中又有了語言,意義不再是堅硬的石壁,而是其中往外滲的水,似有若無,溫柔地滋潤。
時間有連續性,總是向前累積,重新創作是把說完了又說、古老而經典的故事重新說一遍,人人都有說故事的方法,在羊皮紙上用自己的筆劃疊加累積,前人的痕跡模糊了卻又隱約可見,後人的筆跡又與前人的交錯重疊;每個人,在無限大的創作宇宙中,如何打撈自己閃爍的寶藏?
潘Sir說起另一種藝術形式,雕塑。同樣是經過千錘百煉的敲打,一塊石頭才成為了一尊雕塑。在敲打與挖掘之中想要傳達的是什麼?中式雕塑與西式雕塑大有不同,西式雕塑,講究精緻地模仿人的臉容表情、肌肉線條;中式雕塑,則以相對平面的亞洲人臉容為雕塑對象,探尋是如何傳遞人的精神。畫家陳丹青形容,中式雕塑著重「高度概括」和「去除所有多餘細節」,如同京劇中的臉譜化,或山水畫對意境的捕捉,或古典詩歌的言有盡而意無窮。
改編這回事,「重創」這回事,核心都在於對人性,對精神,對意境的追求,在情節之內,語言之外,挖掘埋藏在不同創作之中的人性寶藏。無論哪一個時代,在故事與歷史之中,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所有「人」都走在同一條路上。之前與之後的拐點,若離開道路遠一點去看,彎路看來也像一條直路,而再離得遠一點去看,又或許生命是一個圓,每次拐彎都向著起點更靠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