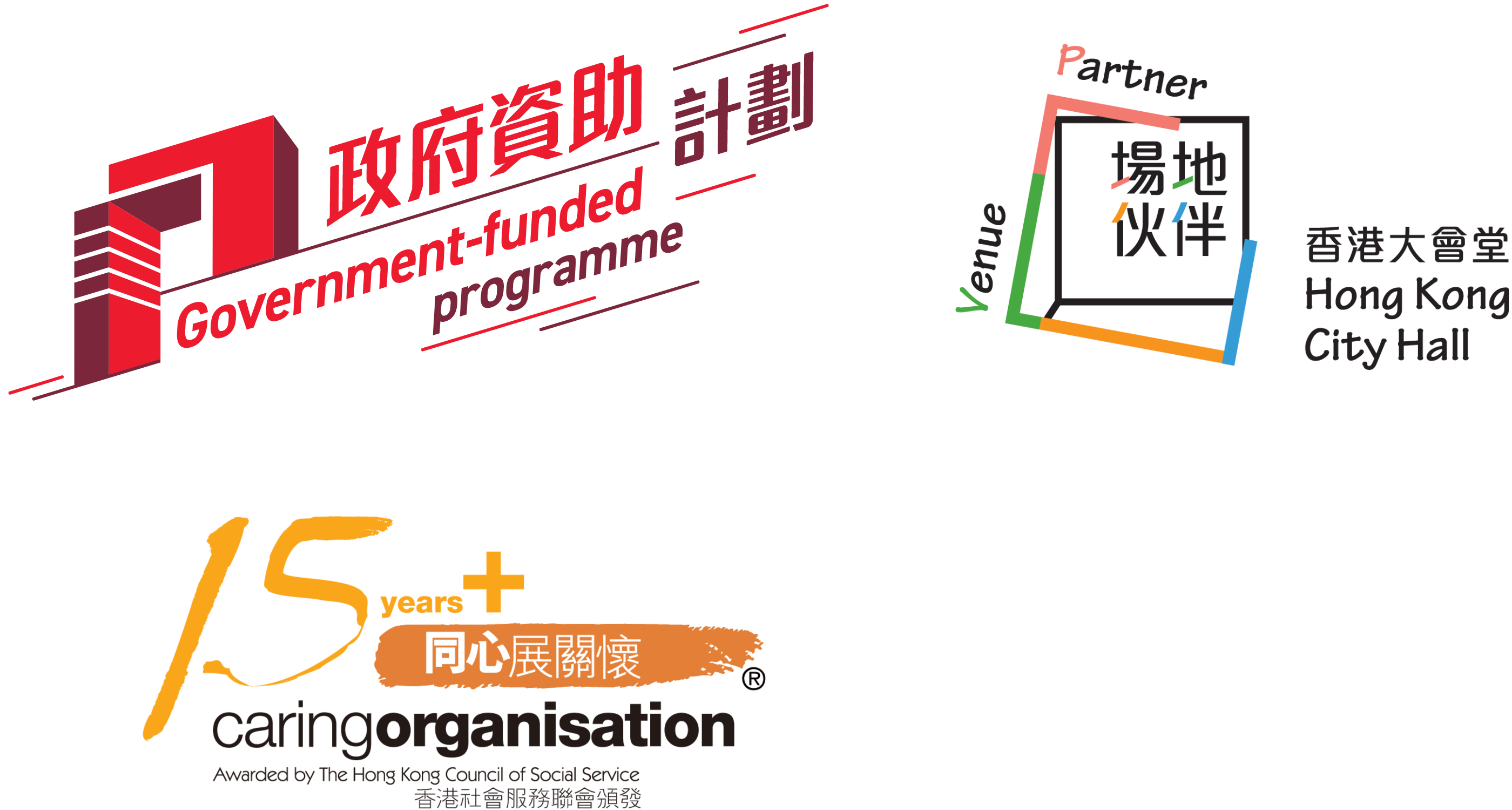戲劇文學
家庭中不能承受的愛
為《兒子》寫文章,就好像為這個案寫「牌板」。假設劇中的兒子是轉介給我的個案,今次經歷就是一次特別的「面見」── 我不是在診症室與兒子對話,而是直接參與他的生活。
兒子
Nicolas 咬著手指甲、不安地出場,焦慮的情緒大概已經浮現。家庭和成長的壓力令他喘不過氣。「我唔知」和不回應是他與父母的溝通方式。但仔細觀察Nicolas 的生活,他似乎是了解自己的需要的。年紀輕輕,他能夠表達感到生活沉重,懂得說出自己的需要,看來他在努力運用自己的資源處理困難。
父親──兒子──母親──繼母
Nicolas 的行為令已經分開了的父母逼於無奈要坐下來「解決問題」。父母的方法都不外乎是「做啲嘢」,為他安排他們覺得是正面的生活方式。可惜父母不單沒有及時察覺他的吶喊並尋求專業人士協助,反而把他捲入一個又一個的情緒漩渦。表面上,他們之間有著愛的互動,但同時,日常溝通卻充滿著張力和矛盾,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單看著也感到疲累。明明不想互相責備,卻又會在話語中表達厭惡;明明是一個充滿愛的畫面,下一秒可以變成一頓吵架場面。可見激烈情緒正潛藏在關係中,一觸即發。這種高度敏感的家庭關係,反映這個家庭已經病入膏肓。
劇中三位成年人,他們受著互相虧欠的捆綁。愛、被愛、背叛與憎恨成為了他們生命的重心。他們來不及亦無力處理自己的問題,更何況要處理兒子的複雜情況。Pierre 努力成為父親,卻討厭這個角色;Anne 正面對丈夫的離開,而兒子卻是下一個離開她的人;Sofia 以為建立了幸福家庭,幸福卻像手中的沙一樣抓不住。他們渴望掌握生活,但生活卻在掌握外。越不能掌握,便越要竭力成為主宰者,以至他們會用各樣在成人世界裡慣用的操控方法去控制其他人的思想、感受和行為。可憐的Nicolas 自覺是父親的負累,知道自己令母親生活在地獄中,感到被繼母拒絕和懷疑,而他卻只會坦蕩蕩地表達需要愛和被愛。試問年紀輕輕的他,又如何能招架這些關係上的矛盾和情緒上的操控?
慶幸這個家庭不是我的真實個案。劇場的力量和演員的震撼演繹帶出人生的殘酷。我眼巴巴看著Nicolas孤獨地走進情緒的深淵,越看越激動。原來走得太近,反而令我失去客觀和感到力不從心。
從死結的束縛中解脫
在我面前的病人,他們的生命往往已經打了很多個結。我經常會問,如果可以早點介入,他們的問題是否可以被及時處理?不過,在這次參與《兒子》的過程,卻讓我自問:現在我可以參與整個「病」的發展,究竟在哪一個階段可以讓我早一點介入,令結局可以改寫?我的反思是:每位家庭成員的人生本來已經有很多個結。他們的互動,又再引發另外的無數個結。而這些結又會一個個以幾何級數的複雜程度和數量去加諸下一代身上……各位可能會感到一份無奈感。而正正,臨床工作確實是充滿無奈:無奈為甚麼家庭中的悲劇會不斷延續下去?不過,無奈並不代表我感到無助。這種無奈感推動我反思:個人困擾、家庭問題、人際關係中的矛盾似乎在生命中無止境地延續,一個個惡性循環的死結,如何能夠被解開?
結,從來都是可以被解開的。結最後會變成死結,是因為只「看」到它很複雜便放棄解下去。所以,「看」、「如何看」、「如何彈性地看」是解結的關鍵。有些人站在逆境當前已經感到疲累,就讓問題繼續滾大,以為可以等待逆境消失、順境出現。結果順境遲遲也不出現,無助、無望感卻把逆境放大到令人選擇放棄。
誠然,逆境其實也相當有用。強而有力的韌力(resilience),正是在逆境中生長出來。在陪伴病人走過幽谷時,我常常體驗到強大韌力所發揮的力量。這力量不會令逆境消失,卻可以令我們在逆境的暴風中站穩,令我們在迷宮中找到方向,令我們越走越強大,令我們能夠感同身受,令我們願意放低自己,推動我們抱持對美好世界的願望。惡性循環得以打斷,正是由這種利他的(altruistic)動機開始。利他美德推動我們留意生活𥚃有毒的溝通方法,例如惡言相向、向身邊的人進行情緒勒索──即有目的地利用對方對關係的重視製造恐懼和罪疚感,讓對方感到難受來操控他的行為和決定以達成自己的目的。當我們越是有強大的心去站在苦難當中,就越能夠看到自己是如何被這些劇毒侵蝕。然而,施毒者往往是被侵蝕得最厲害的一群。
既然看清了,大家便下定決心在這一刻淨化有毒的人際關係吧。由自己開始,敏銳地檢視腦海中的動機、留意從自己口中出來的說話。另一方面,也要留意自己的情緒、思想和行為是否被人不知不覺地操控。慢慢地,我們便可以從人際關係的捆綁中掙脫出來。日子有功,我們更能成為家庭、朋友和社會的清泉。
《兒子》中有一句經常出現的對白:「無事㗎,放心。」我們也愛這樣逃避現實。結果,結,越結越死。《兒子》令我們在劇院裡共處兩小時,逃避不了;既然如此,倒不如我們一起勇敢地去面對吧。現場每一位觀眾都不孤獨,舞台上呈現的殘酷和矛盾,我敢說,台下沒有一個人會感到陌生。劇場的力量,正是把生活精煉濃縮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把我們的所有感官啟動起來去反思生命。
越真實殘酷,越催逼我們看清;越勇敢去看清,越能夠在暴風中站穩。
兒子
Nicolas 咬著手指甲、不安地出場,焦慮的情緒大概已經浮現。家庭和成長的壓力令他喘不過氣。「我唔知」和不回應是他與父母的溝通方式。但仔細觀察Nicolas 的生活,他似乎是了解自己的需要的。年紀輕輕,他能夠表達感到生活沉重,懂得說出自己的需要,看來他在努力運用自己的資源處理困難。
父親──兒子──母親──繼母
Nicolas 的行為令已經分開了的父母逼於無奈要坐下來「解決問題」。父母的方法都不外乎是「做啲嘢」,為他安排他們覺得是正面的生活方式。可惜父母不單沒有及時察覺他的吶喊並尋求專業人士協助,反而把他捲入一個又一個的情緒漩渦。表面上,他們之間有著愛的互動,但同時,日常溝通卻充滿著張力和矛盾,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單看著也感到疲累。明明不想互相責備,卻又會在話語中表達厭惡;明明是一個充滿愛的畫面,下一秒可以變成一頓吵架場面。可見激烈情緒正潛藏在關係中,一觸即發。這種高度敏感的家庭關係,反映這個家庭已經病入膏肓。
劇中三位成年人,他們受著互相虧欠的捆綁。愛、被愛、背叛與憎恨成為了他們生命的重心。他們來不及亦無力處理自己的問題,更何況要處理兒子的複雜情況。Pierre 努力成為父親,卻討厭這個角色;Anne 正面對丈夫的離開,而兒子卻是下一個離開她的人;Sofia 以為建立了幸福家庭,幸福卻像手中的沙一樣抓不住。他們渴望掌握生活,但生活卻在掌握外。越不能掌握,便越要竭力成為主宰者,以至他們會用各樣在成人世界裡慣用的操控方法去控制其他人的思想、感受和行為。可憐的Nicolas 自覺是父親的負累,知道自己令母親生活在地獄中,感到被繼母拒絕和懷疑,而他卻只會坦蕩蕩地表達需要愛和被愛。試問年紀輕輕的他,又如何能招架這些關係上的矛盾和情緒上的操控?
慶幸這個家庭不是我的真實個案。劇場的力量和演員的震撼演繹帶出人生的殘酷。我眼巴巴看著Nicolas孤獨地走進情緒的深淵,越看越激動。原來走得太近,反而令我失去客觀和感到力不從心。
從死結的束縛中解脫
在我面前的病人,他們的生命往往已經打了很多個結。我經常會問,如果可以早點介入,他們的問題是否可以被及時處理?不過,在這次參與《兒子》的過程,卻讓我自問:現在我可以參與整個「病」的發展,究竟在哪一個階段可以讓我早一點介入,令結局可以改寫?我的反思是:每位家庭成員的人生本來已經有很多個結。他們的互動,又再引發另外的無數個結。而這些結又會一個個以幾何級數的複雜程度和數量去加諸下一代身上……各位可能會感到一份無奈感。而正正,臨床工作確實是充滿無奈:無奈為甚麼家庭中的悲劇會不斷延續下去?不過,無奈並不代表我感到無助。這種無奈感推動我反思:個人困擾、家庭問題、人際關係中的矛盾似乎在生命中無止境地延續,一個個惡性循環的死結,如何能夠被解開?
結,從來都是可以被解開的。結最後會變成死結,是因為只「看」到它很複雜便放棄解下去。所以,「看」、「如何看」、「如何彈性地看」是解結的關鍵。有些人站在逆境當前已經感到疲累,就讓問題繼續滾大,以為可以等待逆境消失、順境出現。結果順境遲遲也不出現,無助、無望感卻把逆境放大到令人選擇放棄。
誠然,逆境其實也相當有用。強而有力的韌力(resilience),正是在逆境中生長出來。在陪伴病人走過幽谷時,我常常體驗到強大韌力所發揮的力量。這力量不會令逆境消失,卻可以令我們在逆境的暴風中站穩,令我們在迷宮中找到方向,令我們越走越強大,令我們能夠感同身受,令我們願意放低自己,推動我們抱持對美好世界的願望。惡性循環得以打斷,正是由這種利他的(altruistic)動機開始。利他美德推動我們留意生活𥚃有毒的溝通方法,例如惡言相向、向身邊的人進行情緒勒索──即有目的地利用對方對關係的重視製造恐懼和罪疚感,讓對方感到難受來操控他的行為和決定以達成自己的目的。當我們越是有強大的心去站在苦難當中,就越能夠看到自己是如何被這些劇毒侵蝕。然而,施毒者往往是被侵蝕得最厲害的一群。
既然看清了,大家便下定決心在這一刻淨化有毒的人際關係吧。由自己開始,敏銳地檢視腦海中的動機、留意從自己口中出來的說話。另一方面,也要留意自己的情緒、思想和行為是否被人不知不覺地操控。慢慢地,我們便可以從人際關係的捆綁中掙脫出來。日子有功,我們更能成為家庭、朋友和社會的清泉。
《兒子》中有一句經常出現的對白:「無事㗎,放心。」我們也愛這樣逃避現實。結果,結,越結越死。《兒子》令我們在劇院裡共處兩小時,逃避不了;既然如此,倒不如我們一起勇敢地去面對吧。現場每一位觀眾都不孤獨,舞台上呈現的殘酷和矛盾,我敢說,台下沒有一個人會感到陌生。劇場的力量,正是把生活精煉濃縮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把我們的所有感官啟動起來去反思生命。
越真實殘酷,越催逼我們看清;越勇敢去看清,越能夠在暴風中站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