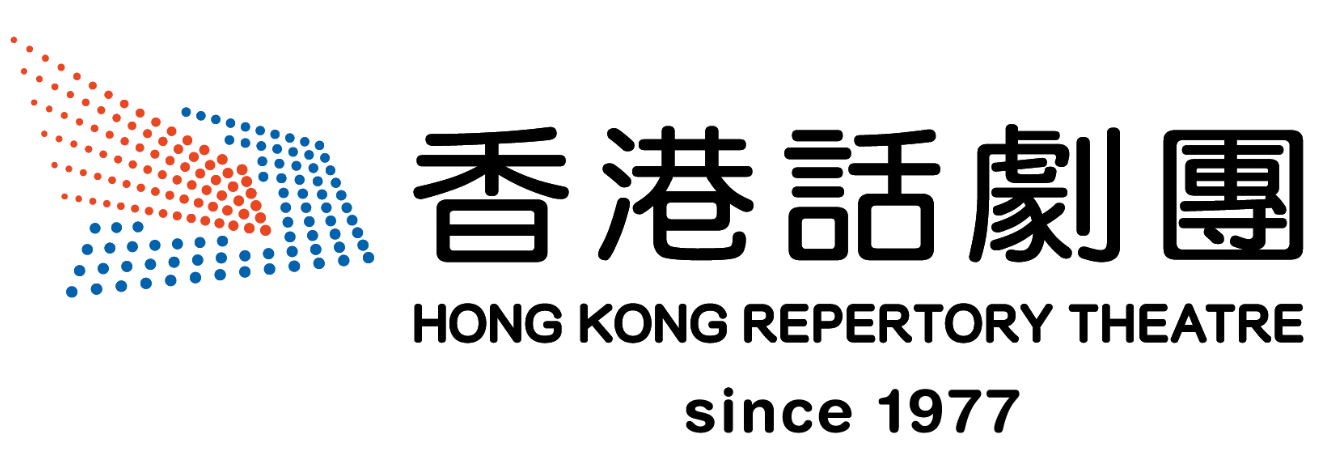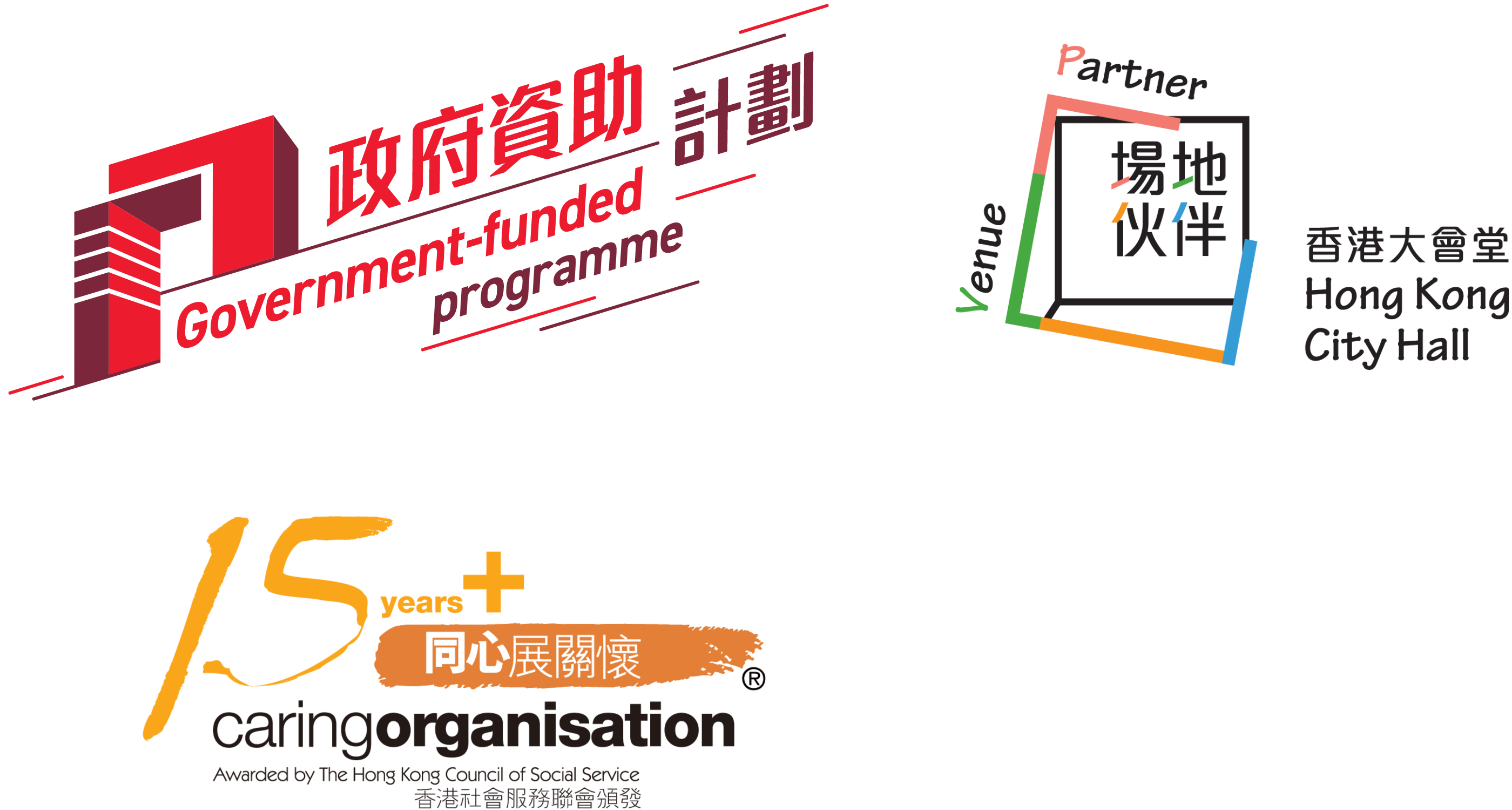2024-25年度「風箏計劃」編劇眼中的編劇
09.03.2025
2024-25年度「風箏計劃」公開演讀
編劇眼中的編劇
2024-25年度「風箏計劃」從近百份華文劇本投稿中,精選八部作品進入公開演讀階段。這些作品風格迥異,涵蓋從兩人密室的心理博弈,到充滿奇幻想像的未來場景;從古人傳記的新編重構,到挑戰生活的現實隱喻,每一部作品都如同一顆尚待雕琢的寶石。
特別策劃的欄目「編劇眼中的編劇」,邀請八位在讀或新晉編劇,以他們的創作視角和生活體悟,剖析這些作品的內在魅力與劇作人的巧思。劇作者們的解讀不僅是對文本的探索,更是一場編劇之間跨越時空的對話,希望藉此點燃更多人對劇本創作的熱誠,讓更多優秀的編劇以及其原創劇目得以被發現,像風箏般翱翔。
一月:花裡看世界
《忘年》:一場有關距離與成長的歷程「風箏計劃」一月 公開演讀《忘年》紀錄文章
「風箏計劃」一月 公開演讀《忘年》紀錄文章
《忘年》為香港話劇團2024-25年度「風箏計劃」入選的原創劇本之一,編劇為林澤銘,這次以劇本演讀的形式展現於觀眾面前。
故事講述60年代生的Daniel(DT),與90年代生的Daniel(DK)一段相差三十一年的忘年戀,在不同的人生歷程中,追求同步卻永不同步的故事。到底,人生之中是否真的能夠達到同步呢?
(1) 起步點差距的三十一年與不斷前進的十五年零六個月
DT與DK兩人年齡差距三十一年,而劇本橫跨十五年六個月。筆者覺得劇本彷彿把兩個角色放在一條時間線上,一前一後,兩者不斷向前行,而觀眾期待的,就是兩人最終是否能夠在時間線上相遇。
事實上,劇本在第一場就透過兩人的對話,表面在討論性,而實際上就是暗示出劇本的核心:
在兩人相處的十五年零六個月裡,兩人分別經歷了人生不同的課題。成熟的DT經歷了與相處多年的同性伴侶分開、退休、移居、年老到伴侶患病;年輕的DK則經歷了學生會事件、朋友離世、理想幻滅、親人老去、身患重病到養子逝世。兩人人生當中經歷大大小小的課題,而這些安排亦足見編劇的巧思。DT曾經說過:
但在編劇的安排下,兩人人生的經歷卻剛剛相反,這不禁令人反思:這些有關年齡的種種「理所當然」又是否必然呢?又是否年老的一定比年輕的經歷得多?實際年齡是否衡量一個人是否成熟的唯一指標?也許正如DK在劇中所言:「唔係大啲嗰個先會阻住人同拖累人。邊個大啲邊個細啲,其實都冇分別。」
有趣的是,去到劇本的最後,面對養子的離世,DT與DK依然有不同的態度,DT離開,DK多年後仍未能釋懷,兩人的距離或許拉近了,但彷彿依然未能同步。而這又帶出一個問題:兩個人相處是否必然需要同步、是否必需要同在呢?或許正如劇中的DT與DK一樣,互相陪伴著大家經歷不同的人生課題,或許會在不同的時段消失,但是又會在不同的時間點重遇,這不是已經很足夠嗎?
(2) DK:一個少年的成長故事
除了DK與DT兩人的關係外,劇本對DK這個少年亦有深刻的描述。DK在劇本之初是一個充滿自信、對生活有要求,理想滿滿的少年,對戰爭、革命、政變、軍事充滿興趣,認為這樣才可以知道「啲老嘢點樣 fuck up 呢個世界」。
但是當他經歷人生的種種生離死別,面對社會現實,昔日主動放棄學位的他要再次考取學歷,希望可以在博物館爭取更高的職位,面對關於「戰爭、革命、政變、軍事」的相片時,不斷自我懷疑,開始對自己一直以來的價值觀產生疑惑。一場一場地看著DK改變,觀眾彷彿與DK一同經歷了一段少年的成長史。
而最令筆者觸動的是劇本的結尾,兩人多年後重新談到養子的死亡,DT不禁悲從中來,蜷縮在墓碑前,崩潰似地哭了起來,然後DK對DT說:「真係冇嘢喎。係咁㗎喎。呢啲嘢,好正常㗎喎。」昔日的少年已經三十多歲,也許明白到人生的生離死別,但是明白不代表接受,亦不代表放下。編劇這一筆充滿著人生的況味。
(3) 編劇的挑戰與巧思
在演後座談會中,編劇林澤銘表示,劇本其中一個希望達到的,是每一場都不要提及當中的時間,讓觀眾在角色的對話與表現中感受時間的流逝。這令筆者想起Patrick Marber的Closer以及Harold Pinter的Betrayal,兩者同樣模糊了場與場之間過度了的時間,透過角色之間的關係等線索暗示時間的流逝。
這種處理方法可以帶來觀賞的趣味,但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會造成混亂。而筆者認為編劇這次的處理是有效的。編劇在劇本中運用了不少巧思來暗示時間的流逝,例如DK開始有視力問題,需要帶眼鏡;DK因為健康問題,吃朱古力時要抄下當中的卡路里;兒童遊樂場與大廈的拆卸等。編劇成功透過人物與環境的改變,暗示時間的流動。
編劇亦善於運用情景,象徵人物的關係及狀況。例如第六場在博物館關燈後,在一片黑暗之中DK亮起手電筒,與DT一同離去,就暗示著DT陪同DK漸漸走出人生黑暗。又例如第八場,DT遠在加拿大與身處香港的DK進行即時視像通訊,訊號的接收不良,彷彿就暗示著兩人接觸不良,不能同步的人生階段。
所以筆者認為,《忘年》是人物形象豐富、具內容深度並且技巧上充滿巧思的作品,就像靈動的風箏,令人期待它越飛越高,讓更多的觀眾可以看到。
黎曜銘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於2020年獲得第六屆青年編劇劇本寫作計劃季軍。
寫劇本,劇場作品包括香港話劇團《人間》、《初三》;劇場空間《Ellie, My Love》(獲第十四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劇本提名)、《隱身的X》;影話戲《灰姑娘と金閣寺》、《扣題》、《療養院的730天》;普劇場《怪の物語》、《怪物》、《彼德與影子的奇幻之旅》。
故事講述60年代生的Daniel(DT),與90年代生的Daniel(DK)一段相差三十一年的忘年戀,在不同的人生歷程中,追求同步卻永不同步的故事。到底,人生之中是否真的能夠達到同步呢?
(1) 起步點差距的三十一年與不斷前進的十五年零六個月
DT與DK兩人年齡差距三十一年,而劇本橫跨十五年六個月。筆者覺得劇本彷彿把兩個角色放在一條時間線上,一前一後,兩者不斷向前行,而觀眾期待的,就是兩人最終是否能夠在時間線上相遇。
事實上,劇本在第一場就透過兩人的對話,表面在討論性,而實際上就是暗示出劇本的核心:
DK: 總之全晚我哋就會係咁等到對方得為止。我得嘅時候你又唔得,你得嘅時候我又唔得,永遠都冇可能同步。
DT: 咁今日等唔到,咪聽日囉。
在兩人相處的十五年零六個月裡,兩人分別經歷了人生不同的課題。成熟的DT經歷了與相處多年的同性伴侶分開、退休、移居、年老到伴侶患病;年輕的DK則經歷了學生會事件、朋友離世、理想幻滅、親人老去、身患重病到養子逝世。兩人人生當中經歷大大小小的課題,而這些安排亦足見編劇的巧思。DT曾經說過:
「你第時搭得最多嘅會係飛機,因為你會想周圍去,而我搭得最多嘅會係巴士因為有兩蚊。你會不斷有朋友嘅婚禮要去,而我只會係咁去朋友嘅葬禮。」
但在編劇的安排下,兩人人生的經歷卻剛剛相反,這不禁令人反思:這些有關年齡的種種「理所當然」又是否必然呢?又是否年老的一定比年輕的經歷得多?實際年齡是否衡量一個人是否成熟的唯一指標?也許正如DK在劇中所言:「唔係大啲嗰個先會阻住人同拖累人。邊個大啲邊個細啲,其實都冇分別。」
有趣的是,去到劇本的最後,面對養子的離世,DT與DK依然有不同的態度,DT離開,DK多年後仍未能釋懷,兩人的距離或許拉近了,但彷彿依然未能同步。而這又帶出一個問題:兩個人相處是否必然需要同步、是否必需要同在呢?或許正如劇中的DT與DK一樣,互相陪伴著大家經歷不同的人生課題,或許會在不同的時段消失,但是又會在不同的時間點重遇,這不是已經很足夠嗎?
(2) DK:一個少年的成長故事
除了DK與DT兩人的關係外,劇本對DK這個少年亦有深刻的描述。DK在劇本之初是一個充滿自信、對生活有要求,理想滿滿的少年,對戰爭、革命、政變、軍事充滿興趣,認為這樣才可以知道「啲老嘢點樣 fuck up 呢個世界」。
但是當他經歷人生的種種生離死別,面對社會現實,昔日主動放棄學位的他要再次考取學歷,希望可以在博物館爭取更高的職位,面對關於「戰爭、革命、政變、軍事」的相片時,不斷自我懷疑,開始對自己一直以來的價值觀產生疑惑。一場一場地看著DK改變,觀眾彷彿與DK一同經歷了一段少年的成長史。
而最令筆者觸動的是劇本的結尾,兩人多年後重新談到養子的死亡,DT不禁悲從中來,蜷縮在墓碑前,崩潰似地哭了起來,然後DK對DT說:「真係冇嘢喎。係咁㗎喎。呢啲嘢,好正常㗎喎。」昔日的少年已經三十多歲,也許明白到人生的生離死別,但是明白不代表接受,亦不代表放下。編劇這一筆充滿著人生的況味。
(3) 編劇的挑戰與巧思
在演後座談會中,編劇林澤銘表示,劇本其中一個希望達到的,是每一場都不要提及當中的時間,讓觀眾在角色的對話與表現中感受時間的流逝。這令筆者想起Patrick Marber的Closer以及Harold Pinter的Betrayal,兩者同樣模糊了場與場之間過度了的時間,透過角色之間的關係等線索暗示時間的流逝。
這種處理方法可以帶來觀賞的趣味,但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會造成混亂。而筆者認為編劇這次的處理是有效的。編劇在劇本中運用了不少巧思來暗示時間的流逝,例如DK開始有視力問題,需要帶眼鏡;DK因為健康問題,吃朱古力時要抄下當中的卡路里;兒童遊樂場與大廈的拆卸等。編劇成功透過人物與環境的改變,暗示時間的流動。
編劇亦善於運用情景,象徵人物的關係及狀況。例如第六場在博物館關燈後,在一片黑暗之中DK亮起手電筒,與DT一同離去,就暗示著DT陪同DK漸漸走出人生黑暗。又例如第八場,DT遠在加拿大與身處香港的DK進行即時視像通訊,訊號的接收不良,彷彿就暗示著兩人接觸不良,不能同步的人生階段。
所以筆者認為,《忘年》是人物形象豐富、具內容深度並且技巧上充滿巧思的作品,就像靈動的風箏,令人期待它越飛越高,讓更多的觀眾可以看到。
作者簡介
黎曜銘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於2020年獲得第六屆青年編劇劇本寫作計劃季軍。
寫劇本,劇場作品包括香港話劇團《人間》、《初三》;劇場空間《Ellie, My Love》(獲第十四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劇本提名)、《隱身的X》;影話戲《灰姑娘と金閣寺》、《扣題》、《療養院的730天》;普劇場《怪の物語》、《怪物》、《彼德與影子的奇幻之旅》。
《鋼牙無爪》:戴一世的retainer「風箏計劃」一月 公開演讀《鋼牙無爪》紀錄文章
「風箏計劃」一月 公開演讀《鋼牙無爪》紀錄文章
受牙痛折磨的女子,夜晚趕到牙醫診所求醫,本來已經下班的牙醫再三拒絕診症,豈料發生連串意料之外的事,兩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被逼困在診所裡,面面相覷,由此展開劇情。
劇本結構簡單,沒有太刻意、花巧的設計,封閉的空間,時間幅度定在一個晚上,單靠兩個人物之間看似日常瑣碎的對話推進,難度匪淺,劇本卻可以流暢自然地帶出少女的「牙痛」心事。
編劇將女生角色設置成一個傻更更的少女,經常自說自話,甚至有時候有點脫離現實。當牙醫打發女生離開,著她明早來,安排一個免費的檢查,當是錯手整爛retainer (牙齒固定器)的賠償,女生不從,堅持指控牙醫是黑幫,以牙醫之名行非法活摘人體器官之實!劇本中的女生就是這樣一個帶點粗線條的角色,而活到中年的牙醫又是一個看重自己專業,對一雙「靈巧的手」引以為傲的角色,把箍牙是「一種對美的追求」奉為圭臬。
在這個角色排列組合下,有時針鋒相對,互不咬弦;有時二人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錯開對話,而突然之間,又會因著一些語言上的錯位而碰撞,迸發出連番趣味。編劇間中加插廣東話「食字」的冷笑話 ,例如:牙醫打邊爐,女生提醒他食材未熟,牙醫腦筋急轉彎,向女生自我介紹之後道出的一句,「而家熟咗啦」,二人終於真正的對話,暗示兩人關係逐漸走近。看著二人招架對方,也是挺過癮的。
可惜的是,有時候編劇把握到人物在某個處境而引起的笑位,但未有在此之上刻劃人物重要面向。例如,牙醫二十四小時生活在診所,無論上班下班,他戲謔這種生活方式是work from home ,其實正正對應著劇本中描述疫情時期的處境,好一個幽默。
不過幽默歸幽默,到底牙醫是怎樣看待生活、關係,以至外面的世界呢?為甚麼他選擇全天候居住在診所?是因為經歷感情挫敗和前妻去世,創傷之後的逃遁嗎?抑或一如女生所料,牙醫除了專業資格以外,生活無甚嗜好,日日都百無聊賴?劇本未有足夠的提示,只有牙醫輕輕帶過的一句,「一離開咗間診所,就咩都唔係,咩都做唔到」。
對比之下,女生的角色有相當的著墨,少女心事亦成功扣連在「牙痛」的意象。牙齒作為全劇的骨幹,去到第三場才逐漸浮現,揭露角色慾望。女生箍牙之後,中間有五年沒有按指示戴retainer ,結果令牙齒移位。現在的她,執著還原七年前箍好牙的完美模樣,渴望將最靚最好的自己送給男朋友。就在這一晚,男朋友向自己提出分手,令女生發現,要戴足一世的retainer 始終無辦法箍住一段變幻無常的感情關係,牙齒會走樣,關係亦然。女生強行將retainer 戴在已經不再如初的牙齒上,這份執著正正是造成她牙痛的肇因。以「牙痛」作喻,穿連起率真可愛的少女愛情觀。
牙醫的愛情觀,大抵就是見於他提及過的前妻,和幫她箍牙後的燦爛笑容,而他抗拒新式隱形牙箍,堅持用傳統鋼線牙箍,與客人建立信任與關係,似乎意有所指,但未明確指出。牙醫角色點點散落在劇本各處,卻欠缺一道針線把牙醫每一點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都穿起來。既然全劇以「牙痛」為起點,實寫關係,那麼牙醫這個身分,如何與整個劇本的骨幹拉上關係呢?筆者下筆之際,依然在思考編劇經營角色的心思。如果可以更深刻挖掘角色的往事,使他們更立體,相信在劇本的收尾,兩個角色的轉變時機亦不會過於突兀。
張沚鈴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一級榮譽),副修文化管理。現就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主修編劇。
在劇場默默耕耘,暫時結果實的:香港藝術節@大館《那些巨大與微小的》(2024)製作演出盒子及演出;曾與創作伙伴共同製作紀實劇場《N個自言自語的人》(2023),擔任文字整理及創作。於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讀劇馬拉松2023世代變奏 :Millennial 」(2023)節目中擔任英國文本《一了百了》(Anatomy of a Suicide)翻譯。
劇本結構簡單,沒有太刻意、花巧的設計,封閉的空間,時間幅度定在一個晚上,單靠兩個人物之間看似日常瑣碎的對話推進,難度匪淺,劇本卻可以流暢自然地帶出少女的「牙痛」心事。
編劇將女生角色設置成一個傻更更的少女,經常自說自話,甚至有時候有點脫離現實。當牙醫打發女生離開,著她明早來,安排一個免費的檢查,當是錯手整爛retainer (牙齒固定器)的賠償,女生不從,堅持指控牙醫是黑幫,以牙醫之名行非法活摘人體器官之實!劇本中的女生就是這樣一個帶點粗線條的角色,而活到中年的牙醫又是一個看重自己專業,對一雙「靈巧的手」引以為傲的角色,把箍牙是「一種對美的追求」奉為圭臬。
在這個角色排列組合下,有時針鋒相對,互不咬弦;有時二人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錯開對話,而突然之間,又會因著一些語言上的錯位而碰撞,迸發出連番趣味。編劇間中加插廣東話「食字」的冷笑話 ,例如:牙醫打邊爐,女生提醒他食材未熟,牙醫腦筋急轉彎,向女生自我介紹之後道出的一句,「而家熟咗啦」,二人終於真正的對話,暗示兩人關係逐漸走近。看著二人招架對方,也是挺過癮的。
可惜的是,有時候編劇把握到人物在某個處境而引起的笑位,但未有在此之上刻劃人物重要面向。例如,牙醫二十四小時生活在診所,無論上班下班,他戲謔這種生活方式是work from home ,其實正正對應著劇本中描述疫情時期的處境,好一個幽默。
不過幽默歸幽默,到底牙醫是怎樣看待生活、關係,以至外面的世界呢?為甚麼他選擇全天候居住在診所?是因為經歷感情挫敗和前妻去世,創傷之後的逃遁嗎?抑或一如女生所料,牙醫除了專業資格以外,生活無甚嗜好,日日都百無聊賴?劇本未有足夠的提示,只有牙醫輕輕帶過的一句,「一離開咗間診所,就咩都唔係,咩都做唔到」。
對比之下,女生的角色有相當的著墨,少女心事亦成功扣連在「牙痛」的意象。牙齒作為全劇的骨幹,去到第三場才逐漸浮現,揭露角色慾望。女生箍牙之後,中間有五年沒有按指示戴retainer ,結果令牙齒移位。現在的她,執著還原七年前箍好牙的完美模樣,渴望將最靚最好的自己送給男朋友。就在這一晚,男朋友向自己提出分手,令女生發現,要戴足一世的retainer 始終無辦法箍住一段變幻無常的感情關係,牙齒會走樣,關係亦然。女生強行將retainer 戴在已經不再如初的牙齒上,這份執著正正是造成她牙痛的肇因。以「牙痛」作喻,穿連起率真可愛的少女愛情觀。
牙醫的愛情觀,大抵就是見於他提及過的前妻,和幫她箍牙後的燦爛笑容,而他抗拒新式隱形牙箍,堅持用傳統鋼線牙箍,與客人建立信任與關係,似乎意有所指,但未明確指出。牙醫角色點點散落在劇本各處,卻欠缺一道針線把牙醫每一點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都穿起來。既然全劇以「牙痛」為起點,實寫關係,那麼牙醫這個身分,如何與整個劇本的骨幹拉上關係呢?筆者下筆之際,依然在思考編劇經營角色的心思。如果可以更深刻挖掘角色的往事,使他們更立體,相信在劇本的收尾,兩個角色的轉變時機亦不會過於突兀。
作者簡介
張沚鈴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一級榮譽),副修文化管理。現就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主修編劇。
在劇場默默耕耘,暫時結果實的:香港藝術節@大館《那些巨大與微小的》(2024)製作演出盒子及演出;曾與創作伙伴共同製作紀實劇場《N個自言自語的人》(2023),擔任文字整理及創作。於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讀劇馬拉松2023世代變奏 :Millennial 」(2023)節目中擔任英國文本《一了百了》(Anatomy of a Suicide)翻譯。
《曠野》:一趟沒有目的地的旅程「風箏計劃」一月 公開演讀《曠野》紀錄文章
「風箏計劃」一月 公開演讀《曠野》紀錄文章
一個孩子自殺的原因會是什麼?《曠野》認為,不回答這個問題才是父母對孩子最好的悼念。《曠野》以非線性的結構,淡然含蓄的語言以及諸多寫意的手法講述一對已離婚的男女發現女兒自殺後,逐漸坦誠自我,與自己、對方以及女兒和解,找到「帶上女兒繼續生活」的方式,這一個過程。
第三視角看自殺
不同於許多從自我視角,在「自殺之前」切入「自殺」問題的戲劇,《曠野》從他者視角觀察「自殺之後」接續的故事。大量從自我視角討論「自殺」的戲劇大篇幅刻畫角色自殺的原因,展露戲劇對人類精神狀態問題的關注。美國劇作家Marsha Norman的《晚安,媽媽》(Night, Mother)是一個女兒自殺前與母親的臨終談話記錄 ─ 這些對話揭露了形塑女兒「自殺」這一決定的過往人生:她婚姻失敗,和家人朋友關係疏遠,患有癲癇讓她完全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英國劇作家Sarah Kane的《4.48精神崩潰》(4.48 Psychosis)中支離破碎的語言折射出主角與俗世毫不兼容的自我是她選擇離開的原因。
以「女兒自殺」為背景的《曠野》未有點明女兒自殺的原因。編劇認為,當事人的消亡已經成為不可改變的過去,所以自殺原因不影響當下和未來。另外,人生不一定會有明確的答案。對於男女主角而言,女兒自殺的原因就是他們人生中不可能被解答的謎。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當事人的心理狀態,所以他者對當事人的認知和當事人對自我的認知永遠存在差距。當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選擇自殺,但他者可能無從認知到,所以他者必然對當事人產生的變化甚至毀滅感到迷惘。人們遇到人生中不可知,不可控的變化,找不到變化的原因是人不可能以全知視角看待他人。所以,女兒自殺的原因沒有任何他者,包括男女主角、編劇以及觀眾知道。這不是一部關注「自殺之前」的社會問題或心理分析劇,而意圖探討當事人「自殺之後」,他人如何懷著此事繼續前行。這才是自殺一事給他者帶來的重要課題。
演員和角色設置中的寫意特徵
《曠野》寫明由同一男演員扮演一個男人的多個不同身份以及這個男人的岳父,並由同一女演員扮演一個女人的不同身份、她的女兒以及她的情敵。編劇認為,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擁有不同的身份,處於不同身份對應的不同關係中。劇中有些角色不可能在同一個人身上出現,僅僅因為性別一致就被同一個演員演繹,因為人物不僅受到自己的過往影響,還受自己未曾參與的過往塑造。編劇讓女演員同時飾演女人和第三者,能表明女人如今對男人的怨恨和隔閡源自於男人和第三者的婚外情。女人的父親和丈夫由同一男演員飾演,暗示女人的父女關係和婚姻關係對她施加了類似的影響,共同造成女人目前的心理狀態。女人的父親和丈夫在離開女人時都沒有給女人明確的答案。同樣的不告而別屢次發生,女人逐漸接受這一事實,在面對女兒的離去時決定不再窮求人生的答案,而是帶著未解決的記憶前行。所以雖然她還是在意男人曾經犯的錯誤,但她不再要求男人明確回應她這些事,就可以回家悼念女兒,畢竟,這裡「總歸是他家」。兩名主角,亦即自殺女兒父母過往歲月裡不同的人物以及人物們背後的過往,共同塑造了他們的當下。
在意識中潛行的旅程
《曠野》的敘事結構表明探索生命問題是鉤沉過往的過程。《曠野》不同場次講述不同時段的過往記憶。這些記憶片段不按時間順序展現。比如第四場的情節發生於女兒青春期,第五場的時間點跳回母親少女時期,而第六場的時間又跳到女兒青春期。非線性的敘事結構裡,場次鋪排看似隨意,卻符合意識活動的跳躍特徵。
全劇中,角色並未開展新行動或者以衝突推動情節發展。他們的唯一行動就是發掘過往記憶。過往的某些記憶已經存在,只是長期封存在心底,需要契機喚起。不同記憶片段隱藏在主角的過往裡,作為他們對女兒自殺成因的多種猜測方式,在這趟回憶旅程裡被拾起,拼凑,呈現主角從未意識到的,人生的真實面目。例如,父親翻動女兒的遺物時,找到女兒小時候為他煮雪糕時用的匙羹,想起自己的父愛之情第一次被喚醒的時刻。開場時一直緊閉心門的男人此刻不由自主暴露了自己的真情,令女人也暫時放下因他的婚外情和離去而出現的情感隔閡,由衷地安慰男人,歡迎他歸來。因為男人的真情流露讓她又回到了一切事端尚未發生時,和這個男人漸行漸遠之前。這時她才格外強烈地感覺到,原來在她心裡,不管自己和男人的關係怎麼變化,其實他們一家三口永遠都是世界上最親密的人,不能分離。
總結
獨特的生命觀念令此劇否決對確定性的追尋。女兒到底為什麽自殺,舞台上的女人到底是女人自己還是女兒還是第三者,一場戲結束後,故事會跳到時間線上的哪個地方,答案都不清晰。但正是這種不清晰令《曠野》高度符號化且具有開放性,令人擱置對某一獨立確定通路的追求,接受人生就是曠野,哪裡都是出路,但哪裡都霧氣濛濛,無邊無際。
何其樂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現就讀香港大學文學及文化研究碩士課程。曾參與改編《風塵裡》、《女刑警隊長》等多部電影和電視劇,以及上海靜安戲劇谷、上海國際喜劇節的策劃工作,長期為劇情類自媒體帳號供稿。創作舞台劇劇本《洞》及《恨逝》。
第三視角看自殺
不同於許多從自我視角,在「自殺之前」切入「自殺」問題的戲劇,《曠野》從他者視角觀察「自殺之後」接續的故事。大量從自我視角討論「自殺」的戲劇大篇幅刻畫角色自殺的原因,展露戲劇對人類精神狀態問題的關注。美國劇作家Marsha Norman的《晚安,媽媽》(Night, Mother)是一個女兒自殺前與母親的臨終談話記錄 ─ 這些對話揭露了形塑女兒「自殺」這一決定的過往人生:她婚姻失敗,和家人朋友關係疏遠,患有癲癇讓她完全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英國劇作家Sarah Kane的《4.48精神崩潰》(4.48 Psychosis)中支離破碎的語言折射出主角與俗世毫不兼容的自我是她選擇離開的原因。
以「女兒自殺」為背景的《曠野》未有點明女兒自殺的原因。編劇認為,當事人的消亡已經成為不可改變的過去,所以自殺原因不影響當下和未來。另外,人生不一定會有明確的答案。對於男女主角而言,女兒自殺的原因就是他們人生中不可能被解答的謎。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當事人的心理狀態,所以他者對當事人的認知和當事人對自我的認知永遠存在差距。當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選擇自殺,但他者可能無從認知到,所以他者必然對當事人產生的變化甚至毀滅感到迷惘。人們遇到人生中不可知,不可控的變化,找不到變化的原因是人不可能以全知視角看待他人。所以,女兒自殺的原因沒有任何他者,包括男女主角、編劇以及觀眾知道。這不是一部關注「自殺之前」的社會問題或心理分析劇,而意圖探討當事人「自殺之後」,他人如何懷著此事繼續前行。這才是自殺一事給他者帶來的重要課題。
演員和角色設置中的寫意特徵
《曠野》寫明由同一男演員扮演一個男人的多個不同身份以及這個男人的岳父,並由同一女演員扮演一個女人的不同身份、她的女兒以及她的情敵。編劇認為,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擁有不同的身份,處於不同身份對應的不同關係中。劇中有些角色不可能在同一個人身上出現,僅僅因為性別一致就被同一個演員演繹,因為人物不僅受到自己的過往影響,還受自己未曾參與的過往塑造。編劇讓女演員同時飾演女人和第三者,能表明女人如今對男人的怨恨和隔閡源自於男人和第三者的婚外情。女人的父親和丈夫由同一男演員飾演,暗示女人的父女關係和婚姻關係對她施加了類似的影響,共同造成女人目前的心理狀態。女人的父親和丈夫在離開女人時都沒有給女人明確的答案。同樣的不告而別屢次發生,女人逐漸接受這一事實,在面對女兒的離去時決定不再窮求人生的答案,而是帶著未解決的記憶前行。所以雖然她還是在意男人曾經犯的錯誤,但她不再要求男人明確回應她這些事,就可以回家悼念女兒,畢竟,這裡「總歸是他家」。兩名主角,亦即自殺女兒父母過往歲月裡不同的人物以及人物們背後的過往,共同塑造了他們的當下。
在意識中潛行的旅程
《曠野》的敘事結構表明探索生命問題是鉤沉過往的過程。《曠野》不同場次講述不同時段的過往記憶。這些記憶片段不按時間順序展現。比如第四場的情節發生於女兒青春期,第五場的時間點跳回母親少女時期,而第六場的時間又跳到女兒青春期。非線性的敘事結構裡,場次鋪排看似隨意,卻符合意識活動的跳躍特徵。
全劇中,角色並未開展新行動或者以衝突推動情節發展。他們的唯一行動就是發掘過往記憶。過往的某些記憶已經存在,只是長期封存在心底,需要契機喚起。不同記憶片段隱藏在主角的過往裡,作為他們對女兒自殺成因的多種猜測方式,在這趟回憶旅程裡被拾起,拼凑,呈現主角從未意識到的,人生的真實面目。例如,父親翻動女兒的遺物時,找到女兒小時候為他煮雪糕時用的匙羹,想起自己的父愛之情第一次被喚醒的時刻。開場時一直緊閉心門的男人此刻不由自主暴露了自己的真情,令女人也暫時放下因他的婚外情和離去而出現的情感隔閡,由衷地安慰男人,歡迎他歸來。因為男人的真情流露讓她又回到了一切事端尚未發生時,和這個男人漸行漸遠之前。這時她才格外強烈地感覺到,原來在她心裡,不管自己和男人的關係怎麼變化,其實他們一家三口永遠都是世界上最親密的人,不能分離。
總結
獨特的生命觀念令此劇否決對確定性的追尋。女兒到底為什麽自殺,舞台上的女人到底是女人自己還是女兒還是第三者,一場戲結束後,故事會跳到時間線上的哪個地方,答案都不清晰。但正是這種不清晰令《曠野》高度符號化且具有開放性,令人擱置對某一獨立確定通路的追求,接受人生就是曠野,哪裡都是出路,但哪裡都霧氣濛濛,無邊無際。
作者簡介
何其樂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現就讀香港大學文學及文化研究碩士課程。曾參與改編《風塵裡》、《女刑警隊長》等多部電影和電視劇,以及上海靜安戲劇谷、上海國際喜劇節的策劃工作,長期為劇情類自媒體帳號供稿。創作舞台劇劇本《洞》及《恨逝》。
二月:人生海海
《在一缸大海中活著》的「如水」「風箏計劃」二月 公開演讀《在一缸大海中活著》紀錄文章
「風箏計劃」二月 公開演讀《在一缸大海中活著》紀錄文章
本地著名作家劉以鬯先生在小說《酒徒》中寫下:「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而於《在一缸大海中活著》中,回憶、念想和慾望不只是霧氣和水珠,更似是一襲洶湧的波濤及強力的暗湧,將角色和觀眾都淹沒和束縛於本地人的困頓之中。
劇中有三位「人物」:年將三十歲,為前程和家人惆悵的斌仔;剛滿十八歲,孩時流離失所,患有恐慌症的凱婷;以及疑似有囤積症,其實是大腦患有疾病的阿梅。此劇開首是寫實的:凱婷到男朋友斌仔所居住的公屋單位中密會時,斌仔母親阿梅從垃圾房抬來她的戰利品——一台大型雪櫃。雪櫃卻不慎被卡在大門前,將三人困於堆滿雜物的空間之中。情侶之間的調情,母子之間的針鋒相對,疑似未來婆媳首次見面的尷尬都使人津津樂道。
但隨著第二場開始,魚缸中的金魚們展開交流,各角色又在不同時段沉睡和失眠,構成不同組合挖掘回憶及內心情感,對話更具哲學性、內容變得概念化。人物的交流透露出編劇對「愛慾生死」的見解及探索。對於「愛慾」,編劇將親情、愛情和友情隱含於大大小小的爭執和衝突之中,同時亦明確表達出慾望在人生困頓之下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對於「生死」,這是個龐大而困難的議題,編劇透過金魚和人物的思辨,將「人何以為生存」、「我們正在『生存』還是在『死亡』」等問題直接端到觀眾面前,引人反思自己的生活。
直到劇本結尾,角色面對的回憶及情感正式化作源源不絕的水,直接從雪櫃傾瀉而出,最終將整個場景都浸沒。角色的無奈及無力,透過一片濁水渲染筆者的思緒,即使在風乾過後仍留有痕跡,揮之不去。由此可見,即使編劇捨易取難,放下便利大眾理解的情節發展,執起象徵及比喻作為工具,依然能為人物雕琢出清晰而深刻的生活狀態。
雖然編劇的寫作意念及風格鮮明清晰,但筆者仍對劇中兩個部份感到困惑,望能了解更多作者在選擇目前劇情及角色行動時的思路和原因:
一,故事完結於雪櫃湧出洪水,將斌仔淹沒。斌仔的困局,以及引來的焦躁、煩厭及憤恨,皆源自於拋妻棄子的爸爸、固執己見同時拖累自身的媽媽,以及過往做「錯」決定的自己。比起阿梅從外面不知哪裡抬回家的雪櫃,會否有其他更好的水源,以表現這些負面情緒皆來自斌仔自身的執念?
二,斌仔及阿梅被困於這個「家」之中,當局者迷,所以筆者明白他們因無力而無意打破僵局的決定。但這家的局外人——凱婷呢?她又為何選擇與斌仔一起浸沉在水底?作為於這清晨了解這個家的旁觀者,作為一個只有十八歲的年青人,她會否尚有一息生氣、一絲動力去帶領二人走出這個充斥著污水的家?畢竟求生是每個人的本能,編劇需要用更多筆墨、以更大力度說服觀眾,令觀眾認同凱婷選擇「潛到水底」的決定是無可避免的。
野生動物紀錄片多透過觀察動物捕獵和繁殖以顯示牠們的生命力,而戲劇則透過刻劃人類的選擇及行動展現人性。不論是著重對日常生活的描寫,又抑或採用具哲學性的辯證,觀眾都是通過劇中角色的行動摸索他們的動機,繼而推敲出編劇對人生的見解。當然,採取「不行動」和「躺平」亦是一種行動,甚至更能反映出人的某種生存狀態,但在經歷過一場海嘯過後,在頹垣敗瓦前放肆完情感,裹足不前並非所有人唯一的選擇。角色需要的是甚麼?觀眾想感受到的是甚麼?也許是舉步前行的勇氣及力量。
刁時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現職本地教育工作者,同時就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主修編劇。過往編劇作品包括新域劇團(「劇場裡的臥虎與藏龍」)《活寡》、《血肉之軀》;影話戲《暮逸邨謀殺案》、《在家人》,現亦正參與第八屆青年編劇劇本寫作計劃,新作將於五月發表。
劇中有三位「人物」:年將三十歲,為前程和家人惆悵的斌仔;剛滿十八歲,孩時流離失所,患有恐慌症的凱婷;以及疑似有囤積症,其實是大腦患有疾病的阿梅。此劇開首是寫實的:凱婷到男朋友斌仔所居住的公屋單位中密會時,斌仔母親阿梅從垃圾房抬來她的戰利品——一台大型雪櫃。雪櫃卻不慎被卡在大門前,將三人困於堆滿雜物的空間之中。情侶之間的調情,母子之間的針鋒相對,疑似未來婆媳首次見面的尷尬都使人津津樂道。
但隨著第二場開始,魚缸中的金魚們展開交流,各角色又在不同時段沉睡和失眠,構成不同組合挖掘回憶及內心情感,對話更具哲學性、內容變得概念化。人物的交流透露出編劇對「愛慾生死」的見解及探索。對於「愛慾」,編劇將親情、愛情和友情隱含於大大小小的爭執和衝突之中,同時亦明確表達出慾望在人生困頓之下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對於「生死」,這是個龐大而困難的議題,編劇透過金魚和人物的思辨,將「人何以為生存」、「我們正在『生存』還是在『死亡』」等問題直接端到觀眾面前,引人反思自己的生活。
直到劇本結尾,角色面對的回憶及情感正式化作源源不絕的水,直接從雪櫃傾瀉而出,最終將整個場景都浸沒。角色的無奈及無力,透過一片濁水渲染筆者的思緒,即使在風乾過後仍留有痕跡,揮之不去。由此可見,即使編劇捨易取難,放下便利大眾理解的情節發展,執起象徵及比喻作為工具,依然能為人物雕琢出清晰而深刻的生活狀態。
雖然編劇的寫作意念及風格鮮明清晰,但筆者仍對劇中兩個部份感到困惑,望能了解更多作者在選擇目前劇情及角色行動時的思路和原因:
一,故事完結於雪櫃湧出洪水,將斌仔淹沒。斌仔的困局,以及引來的焦躁、煩厭及憤恨,皆源自於拋妻棄子的爸爸、固執己見同時拖累自身的媽媽,以及過往做「錯」決定的自己。比起阿梅從外面不知哪裡抬回家的雪櫃,會否有其他更好的水源,以表現這些負面情緒皆來自斌仔自身的執念?
二,斌仔及阿梅被困於這個「家」之中,當局者迷,所以筆者明白他們因無力而無意打破僵局的決定。但這家的局外人——凱婷呢?她又為何選擇與斌仔一起浸沉在水底?作為於這清晨了解這個家的旁觀者,作為一個只有十八歲的年青人,她會否尚有一息生氣、一絲動力去帶領二人走出這個充斥著污水的家?畢竟求生是每個人的本能,編劇需要用更多筆墨、以更大力度說服觀眾,令觀眾認同凱婷選擇「潛到水底」的決定是無可避免的。
野生動物紀錄片多透過觀察動物捕獵和繁殖以顯示牠們的生命力,而戲劇則透過刻劃人類的選擇及行動展現人性。不論是著重對日常生活的描寫,又抑或採用具哲學性的辯證,觀眾都是通過劇中角色的行動摸索他們的動機,繼而推敲出編劇對人生的見解。當然,採取「不行動」和「躺平」亦是一種行動,甚至更能反映出人的某種生存狀態,但在經歷過一場海嘯過後,在頹垣敗瓦前放肆完情感,裹足不前並非所有人唯一的選擇。角色需要的是甚麼?觀眾想感受到的是甚麼?也許是舉步前行的勇氣及力量。
作者簡介
刁時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現職本地教育工作者,同時就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主修編劇。過往編劇作品包括新域劇團(「劇場裡的臥虎與藏龍」)《活寡》、《血肉之軀》;影話戲《暮逸邨謀殺案》、《在家人》,現亦正參與第八屆青年編劇劇本寫作計劃,新作將於五月發表。
《逐流》:與徐波分離後的荒誕「風箏計劃」二月 公開演讀《逐流》紀錄文章
「風箏計劃」二月 公開演讀《逐流》紀錄文章
這不是傳統推理戲劇。X3
主角徐波在整個劇本裡,對自己殺人的事只說了一個「好」字,沒有解釋更沒有辯護,編劇知道觀眾求知若渴,就給了幾個角色來側寫主角的平凡世界。
媽媽,她眼中的徐波只是一個「叮噹百寶袋」,為了生活得更好,一切所需也在他那裡予取予攜,甚至兒子抽了居屋想成家立室,她腦裡想起的畫面只是如何與小兒子瓜分徐波的新居,這對她而言是如此合理而平凡。
阿寶,她沒有說出和徐波十三年的愛情是怎樣過的,但當懷有身孕就立即和他斷絕一切關係,既平凡又合理地說明她不能夠和徐波有任何將來。
Matthew,徐波的同事。徐波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脫節為他帶來很大麻煩,討厭為自己帶來負累。疏遠不同頻道的人,在職場既平凡又常見。
但這真的只是平凡嗎?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文譯名的重點是「惡的平凡」。書中的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手上沾滿數以萬計猶太人的血,但他想著的只是如何令生活過得更好,如何升職討好上司,因可以「掹衫尾」進入舉行「萬湖會議」[1]的別墅而沾沾自喜,那怕根本沒有任何高層記得他曾站在場地的牆角。他認為自己只是在做一份平凡的工作,過平凡的人生,就如當時大部份的德國人一樣,也如同劇中的角色一樣,但他們「同質性」地摧毀著別人的人生,徐波只是和社會的標準不同,只是與社會接不上軌,就被社會肆意平凡地壓榨,編劇要給觀眾的不是殺人的理由,而是叩問何以惡是如此平凡。
當觀眾仍鍥而不捨追問殺人原因,編劇到了最後仍只給出一個徐波的夢,反問了一句「原因真的如此重要嗎?」在現代宗教失效,人類以為一切也可以用理性去解釋的時代,人追求凡事總要有個明確的原因,但這習性是低估了人性的複雜,在「蝴蝶效應」下,每個小小的動作也會如核子反應般一發不可收拾,追尋只是徒然,人生本來就是充滿隨機性,這是編劇對於人生的見解。但追尋是人性,沒有原因的行為是人性,而徐波失望的疊加,對未來想像的幻滅,無法融入世界的徬徨,更加是有血有肉的人性,編劇關心的不是徐波殺人的原因,而是關懷徐波這個「人」。
這個「人」,正在反抗現實。
劇作The Maids的作者尚.惹內(Jean Genet),出生於一個法國的單親家庭,童年由兒童救濟機構照顧,這在當時是平凡而常見,但惹內就是無法接受被安排的人生,以及社會的價值規範。他視自己為社會的局外人,雖自小已顯示自己的天賦,但就是不斷的盜竊、使用假證件、流浪、做出猥褻行為,一切當時社會視為罪惡的,視為自毀的行徑,也被惹內視為反抗社會的工具。同樣身為社會局外人的徐波,也以自己的方式——自毀,來反抗這個壓榨他的社會。
而自毀的結果,卻為他帶來了自我救贖。在最後一場,徐波與媽媽在監倉內對話,徐波說「媽,我好鍾意呢度。我有獨立房㗎,我鍾意做咩都得」,他耗盡心力也無法在「自由」社會中求得容身之地,但自毀後卻在「受困」的監倉內得到自己的世界,「自由」與「受困」如何定義?編劇繼續丟下重磅炸彈。
邪惡如此平凡,人生沒有答案,自毀帶來救贖,自由源自受困,這一切看似荒謬,但人生本是如此。編劇逼觀眾直面人生的荒謬,給予的課題相當沉重,雖然劇本仍有很多可進步的空間,但編劇的視野更加珍貴。
[1] 納粹德國官員為討論「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召開的會議,會議期間落實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何家恒
畢業於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現正修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主修編劇。
2016年憑劇本《密室》獲得影話戲「第五屆青年編劇劇本寫作計劃」優異獎、影話戲《一絲不掛》及《Dear,佛系YouTuber》聯合編劇、憑《龜殼,死魚,破地獄》入圍新域劇團「劇場裡的臥虎與藏龍XVI」,並參加影話戲「網上讀劇系列」。
主角徐波在整個劇本裡,對自己殺人的事只說了一個「好」字,沒有解釋更沒有辯護,編劇知道觀眾求知若渴,就給了幾個角色來側寫主角的平凡世界。
媽媽,她眼中的徐波只是一個「叮噹百寶袋」,為了生活得更好,一切所需也在他那裡予取予攜,甚至兒子抽了居屋想成家立室,她腦裡想起的畫面只是如何與小兒子瓜分徐波的新居,這對她而言是如此合理而平凡。
阿寶,她沒有說出和徐波十三年的愛情是怎樣過的,但當懷有身孕就立即和他斷絕一切關係,既平凡又合理地說明她不能夠和徐波有任何將來。
Matthew,徐波的同事。徐波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脫節為他帶來很大麻煩,討厭為自己帶來負累。疏遠不同頻道的人,在職場既平凡又常見。
但這真的只是平凡嗎?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文譯名的重點是「惡的平凡」。書中的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手上沾滿數以萬計猶太人的血,但他想著的只是如何令生活過得更好,如何升職討好上司,因可以「掹衫尾」進入舉行「萬湖會議」[1]的別墅而沾沾自喜,那怕根本沒有任何高層記得他曾站在場地的牆角。他認為自己只是在做一份平凡的工作,過平凡的人生,就如當時大部份的德國人一樣,也如同劇中的角色一樣,但他們「同質性」地摧毀著別人的人生,徐波只是和社會的標準不同,只是與社會接不上軌,就被社會肆意平凡地壓榨,編劇要給觀眾的不是殺人的理由,而是叩問何以惡是如此平凡。
當觀眾仍鍥而不捨追問殺人原因,編劇到了最後仍只給出一個徐波的夢,反問了一句「原因真的如此重要嗎?」在現代宗教失效,人類以為一切也可以用理性去解釋的時代,人追求凡事總要有個明確的原因,但這習性是低估了人性的複雜,在「蝴蝶效應」下,每個小小的動作也會如核子反應般一發不可收拾,追尋只是徒然,人生本來就是充滿隨機性,這是編劇對於人生的見解。但追尋是人性,沒有原因的行為是人性,而徐波失望的疊加,對未來想像的幻滅,無法融入世界的徬徨,更加是有血有肉的人性,編劇關心的不是徐波殺人的原因,而是關懷徐波這個「人」。
這個「人」,正在反抗現實。
劇作The Maids的作者尚.惹內(Jean Genet),出生於一個法國的單親家庭,童年由兒童救濟機構照顧,這在當時是平凡而常見,但惹內就是無法接受被安排的人生,以及社會的價值規範。他視自己為社會的局外人,雖自小已顯示自己的天賦,但就是不斷的盜竊、使用假證件、流浪、做出猥褻行為,一切當時社會視為罪惡的,視為自毀的行徑,也被惹內視為反抗社會的工具。同樣身為社會局外人的徐波,也以自己的方式——自毀,來反抗這個壓榨他的社會。
而自毀的結果,卻為他帶來了自我救贖。在最後一場,徐波與媽媽在監倉內對話,徐波說「媽,我好鍾意呢度。我有獨立房㗎,我鍾意做咩都得」,他耗盡心力也無法在「自由」社會中求得容身之地,但自毀後卻在「受困」的監倉內得到自己的世界,「自由」與「受困」如何定義?編劇繼續丟下重磅炸彈。
邪惡如此平凡,人生沒有答案,自毀帶來救贖,自由源自受困,這一切看似荒謬,但人生本是如此。編劇逼觀眾直面人生的荒謬,給予的課題相當沉重,雖然劇本仍有很多可進步的空間,但編劇的視野更加珍貴。
[1] 納粹德國官員為討論「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召開的會議,會議期間落實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作者簡介
何家恒
畢業於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現正修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主修編劇。
2016年憑劇本《密室》獲得影話戲「第五屆青年編劇劇本寫作計劃」優異獎、影話戲《一絲不掛》及《Dear,佛系YouTuber》聯合編劇、憑《龜殼,死魚,破地獄》入圍新域劇團「劇場裡的臥虎與藏龍XVI」,並參加影話戲「網上讀劇系列」。
生與死的邊緣 —《冰晶兒民》「風箏計劃」二月 公開演讀《冰晶兒民》紀錄文章
「風箏計劃」二月 公開演讀《冰晶兒民》紀錄文章
金魚被-196 ℃的液態氮迅速冷凍,解凍後又成功復生。這是本劇最先呈現給我們的畫面。魚可復生,人是否亦可?《冰晶兒民》以冷凍技術為切入點,叩問科技與生命的邊界。在這個科學飛速發展的時代,人類如何面對生死的抉擇?生命的意義是否會有新的變化?
本劇講了一對夫妻將自己年僅4歲、患腦癌的女兒Einz冷凍的故事。第一幕中採用雙線敘事,一條線是從2013年Einz生病之前開始講述,冷凍前,父母因在冷凍女兒與否的決定上產生分歧。另一條則是2018年Einz被冷凍後,她的哥哥Matrix短暫出家,在寺廟與住持聊天,了解到有關泰國和寺廟所處的地區清邁,也就是金三角的歷史。兩條線以佛教產生聯繫,泰國是大多數國民信仰佛教的國家,而佛教的生死觀和通俗社會不完全一樣,所以在成功冷凍妹妹之後,Matrix一家受到了社會以及民眾的輿論攻擊。第二幕時間線從2015年順序行進,Matrix因輿論攻撃感到困惑入廟修行,之後從天才科學家Robert處了解到妹妹復生概率低微。
在冷凍復生這種現代特殊情況下,生命的意義顯得尤為迷離,在面對生命逝去的時刻,是釋然放手,還是用一絲哪怕非常渺茫的希望去做最後的嘗試?這是生活在泰國的科學家家庭的艱難抉擇。科技發展飛速,然而科技接觸到的未知邊緣也愈來愈多。冷凍、復生、意識上傳,數字生命,這些詞語在新聞中不算陌生,但當自己或家人的生命要經由這些技術來保存時,我們將如何應對?經由這些技術保存的生命,是以怎樣的狀態存活,甚至是不是存活,都是未知狀態。更別說,這樣的生命還是不是之前的生命,這又涉及到生命的本質,即劇中多次提到的「『我』是誰」的問題。這些有關生命和自我的討論經久不衰,在新的現實語境下又有新的發展。新技術對人類的心理和生活的影響是甚麼?在新技術之下生命的意義又在哪裡?
此外,在這部劇開頭就引入了很多物理上的概念,這是很有新意的一點。譬如熵,一個熱力學中衡量混亂度的指標。熱力學上認為在孤立系统中,體系與環境没有能量交換,體系總是自發地向混亂度增大的方向變化,使整個系统的熵值增大。也就是說,如果把整個宇宙看作一個孤立系統,那麼它總是朝熵增,也就是更無序的方向變化,如果宇宙終將歸於熱寂[1],所有的執念是否都沒有意義?編劇有提到想借助冷凍這一動作來討論時間的凝結,當粒子停止運動時,當妹妹處於冷凍時,時間是否仍悄然流逝?
住持以鯉魚與魚塘隱喻泰國局勢,鯉魚或象徵掙扎的民眾,魚塘則暗指動蕩的社會。一家人遭受的攻擊與他們所處的地位和立場有關,而這些人民之間的相互攻擊往往是更高一層的大手在撥弄,正如人生在世,所有的遭遇彷彿也像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撥弄,而這隻手叫做命運,即使是個人的努力和目前的科學,有時也無法左右它。最終,Matrix一家繼續向前生活,能看到編劇想告訴我們的,就是用愛去創造自己的人生目的。
[1] 熱寂:宇宙中的有效能量全數轉化為熱能,所有物質溫度達到熱平衡,宇宙中再沒有任何可以維持運動或是生命的能量存在。
作者簡介
袁月洋
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現就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主修編劇。過往編劇作品包括話劇《一水之遙》(獲第二屆全國小劇場戲劇優秀劇目)、《失去魔法的世界》、《流浪謠》、《我睡了別吵》。
本劇講了一對夫妻將自己年僅4歲、患腦癌的女兒Einz冷凍的故事。第一幕中採用雙線敘事,一條線是從2013年Einz生病之前開始講述,冷凍前,父母因在冷凍女兒與否的決定上產生分歧。另一條則是2018年Einz被冷凍後,她的哥哥Matrix短暫出家,在寺廟與住持聊天,了解到有關泰國和寺廟所處的地區清邁,也就是金三角的歷史。兩條線以佛教產生聯繫,泰國是大多數國民信仰佛教的國家,而佛教的生死觀和通俗社會不完全一樣,所以在成功冷凍妹妹之後,Matrix一家受到了社會以及民眾的輿論攻擊。第二幕時間線從2015年順序行進,Matrix因輿論攻撃感到困惑入廟修行,之後從天才科學家Robert處了解到妹妹復生概率低微。
在冷凍復生這種現代特殊情況下,生命的意義顯得尤為迷離,在面對生命逝去的時刻,是釋然放手,還是用一絲哪怕非常渺茫的希望去做最後的嘗試?這是生活在泰國的科學家家庭的艱難抉擇。科技發展飛速,然而科技接觸到的未知邊緣也愈來愈多。冷凍、復生、意識上傳,數字生命,這些詞語在新聞中不算陌生,但當自己或家人的生命要經由這些技術來保存時,我們將如何應對?經由這些技術保存的生命,是以怎樣的狀態存活,甚至是不是存活,都是未知狀態。更別說,這樣的生命還是不是之前的生命,這又涉及到生命的本質,即劇中多次提到的「『我』是誰」的問題。這些有關生命和自我的討論經久不衰,在新的現實語境下又有新的發展。新技術對人類的心理和生活的影響是甚麼?在新技術之下生命的意義又在哪裡?
此外,在這部劇開頭就引入了很多物理上的概念,這是很有新意的一點。譬如熵,一個熱力學中衡量混亂度的指標。熱力學上認為在孤立系统中,體系與環境没有能量交換,體系總是自發地向混亂度增大的方向變化,使整個系统的熵值增大。也就是說,如果把整個宇宙看作一個孤立系統,那麼它總是朝熵增,也就是更無序的方向變化,如果宇宙終將歸於熱寂[1],所有的執念是否都沒有意義?編劇有提到想借助冷凍這一動作來討論時間的凝結,當粒子停止運動時,當妹妹處於冷凍時,時間是否仍悄然流逝?
住持以鯉魚與魚塘隱喻泰國局勢,鯉魚或象徵掙扎的民眾,魚塘則暗指動蕩的社會。一家人遭受的攻擊與他們所處的地位和立場有關,而這些人民之間的相互攻擊往往是更高一層的大手在撥弄,正如人生在世,所有的遭遇彷彿也像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撥弄,而這隻手叫做命運,即使是個人的努力和目前的科學,有時也無法左右它。最終,Matrix一家繼續向前生活,能看到編劇想告訴我們的,就是用愛去創造自己的人生目的。
[1] 熱寂:宇宙中的有效能量全數轉化為熱能,所有物質溫度達到熱平衡,宇宙中再沒有任何可以維持運動或是生命的能量存在。
作者簡介
袁月洋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現就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主修編劇。過往編劇作品包括話劇《一水之遙》(獲第二屆全國小劇場戲劇優秀劇目)、《失去魔法的世界》、《流浪謠》、《我睡了別吵》。
三月:夜空中最亮的星
《土星來信》:再等一會。「風箏計劃」三月 公開演讀《土星來信》紀錄文章
「風箏計劃」三月 公開演讀《土星來信》紀錄文章
《土星來信》是一個極其溫暖的劇本,暖意撫慰人心。
解開時代下的創傷
故事中兩個主人翁雖然在設定上相差六年,但屬於同一世代,也正面臨生命中不易跨越的狹縫:世俗標準施加無法承受的壓力,令生活脫軌。Seven放低專業前景,投身占星;Tim與世隔絕,背負討厭自己的包袱。
編劇透過Seven為Tim解讀星盤的過程,帶出《土星》的核心意象:每個人都要經歷土星回歸;它既是困境,也是磨練;平靜面對,心存正念,便能蛻變。故事結尾有兩段溫柔極致的獨白,分別是Tim終於將害死流浪貓的創傷娓娓道來,最後放下包袱,原諒在職場失敗的自己;另一段是Seven的來信,既安慰Tim也安慰自己,將土星來襲轉化成面對創傷的契機,便可一步一步走過。
筆者認為《土星》的核心思想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體現出劇場的「解結」能力。可以想像,倘若一個正經歷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壓力的觀眾有緣觀看此劇,那種溫柔、溫暖的絮語、耳語,可能便是救起他的關鍵一手。
故事結構與戲劇行動
故事結構清晰,順理成章,由Seven占星事業的獵奇案例開始,偶然遇到Tim這位奇怪顧客,再慢慢揭開二人的背景故事,觀看時代下小人物的精神面貌。
筆者認為《土星》的高潮並不在於「情節」,而在於「情感」。Tim暈倒是全劇中在「情節」上最大的高潮,它引發後來方小姐的出現,也推動Seven分享自身故事。但筆者認為這個「情節」並非最「緊張」的時刻,此劇最令人「緊張」的,是主人翁能否「透過重述經歷來跟自己和解」——角色鼓起勇氣面對過去的瞬間,才是《土星》最扣人心弦之處。
這種獨特之處構成此劇特色:故事側重剖白過去內容,而非解決眼前困境的戲劇行動。《土星》有不少篇幅由角色剖白過去發生的事情,那些經歷細膩動人,捕捉生命中的微妙時刻,深入人性;但這些內容都發生在「過去」,對「當下」的角色而言,最大的影響是他們的性格和能否面對的「決定」。這可能構成一個情況:觀眾必須對角色的過去有莫大的好奇,才有動力追看故事下去。
絲絲入扣的意象
《土星》意象豐富,充滿詩意;意象之間互相呼應,有趣而不突兀;建構具體記憶點,容易回想和回味。
土星回歸、擾人的水管聲、轉化出來的風鈴聲,和入口酸澀的「幸運糖」,比喻人生不如意事總會渡過(雖然編劇在對白中自嘲「灌雞湯」,但這種溫柔的「灌」法,觀眾比較受落);那隻Tim嘗試拯救最後卻本末倒置的流浪貓,仿佛便是無法與俗世框架契合的Tim,被冠冕堂皇的社會犧牲。筆者最深刻的,是Seven不知從哪裡聞到的臭味;那股可能由自身散發、頹廢、被厭惡的氣息,充滿質感,由文字刺激想像,細膩微妙,而且一針見血。這些意象為《土星》建構一幅豐富的星圖。
結語
筆者認為《土星》是一個發自內心、充滿熱度、處處善意的作品;那股觸及心靈深處的力量,正是當下都市人需要的滋養:再等一會,總會過的。期待她會成為一個更加精煉和具備追看性的作品,在劇場裡散發溫暖的光芒。
李偉樂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主修編劇(優異)。
憑《塵落無聲》提名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IATC(HK)劇評人獎年度劇本/編劇及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劇本。
近年編劇作品:香港話劇圑讀戲劇場《別來無恙》、文本特區《水中不知流》及「新戲匠」系列《病房》;同流《移家女孩2.0》、《今晚,Omakase夜唔夜?》;劇毒演讀劇《蘇拉超人與索奇星怪的第794回》及三色豆劇團演讀劇場《野戰》(聯合編劇)。
現職編劇和戲劇導師。
解開時代下的創傷
故事中兩個主人翁雖然在設定上相差六年,但屬於同一世代,也正面臨生命中不易跨越的狹縫:世俗標準施加無法承受的壓力,令生活脫軌。Seven放低專業前景,投身占星;Tim與世隔絕,背負討厭自己的包袱。
編劇透過Seven為Tim解讀星盤的過程,帶出《土星》的核心意象:每個人都要經歷土星回歸;它既是困境,也是磨練;平靜面對,心存正念,便能蛻變。故事結尾有兩段溫柔極致的獨白,分別是Tim終於將害死流浪貓的創傷娓娓道來,最後放下包袱,原諒在職場失敗的自己;另一段是Seven的來信,既安慰Tim也安慰自己,將土星來襲轉化成面對創傷的契機,便可一步一步走過。
筆者認為《土星》的核心思想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體現出劇場的「解結」能力。可以想像,倘若一個正經歷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壓力的觀眾有緣觀看此劇,那種溫柔、溫暖的絮語、耳語,可能便是救起他的關鍵一手。
故事結構與戲劇行動
故事結構清晰,順理成章,由Seven占星事業的獵奇案例開始,偶然遇到Tim這位奇怪顧客,再慢慢揭開二人的背景故事,觀看時代下小人物的精神面貌。
筆者認為《土星》的高潮並不在於「情節」,而在於「情感」。Tim暈倒是全劇中在「情節」上最大的高潮,它引發後來方小姐的出現,也推動Seven分享自身故事。但筆者認為這個「情節」並非最「緊張」的時刻,此劇最令人「緊張」的,是主人翁能否「透過重述經歷來跟自己和解」——角色鼓起勇氣面對過去的瞬間,才是《土星》最扣人心弦之處。
這種獨特之處構成此劇特色:故事側重剖白過去內容,而非解決眼前困境的戲劇行動。《土星》有不少篇幅由角色剖白過去發生的事情,那些經歷細膩動人,捕捉生命中的微妙時刻,深入人性;但這些內容都發生在「過去」,對「當下」的角色而言,最大的影響是他們的性格和能否面對的「決定」。這可能構成一個情況:觀眾必須對角色的過去有莫大的好奇,才有動力追看故事下去。
絲絲入扣的意象
《土星》意象豐富,充滿詩意;意象之間互相呼應,有趣而不突兀;建構具體記憶點,容易回想和回味。
土星回歸、擾人的水管聲、轉化出來的風鈴聲,和入口酸澀的「幸運糖」,比喻人生不如意事總會渡過(雖然編劇在對白中自嘲「灌雞湯」,但這種溫柔的「灌」法,觀眾比較受落);那隻Tim嘗試拯救最後卻本末倒置的流浪貓,仿佛便是無法與俗世框架契合的Tim,被冠冕堂皇的社會犧牲。筆者最深刻的,是Seven不知從哪裡聞到的臭味;那股可能由自身散發、頹廢、被厭惡的氣息,充滿質感,由文字刺激想像,細膩微妙,而且一針見血。這些意象為《土星》建構一幅豐富的星圖。
結語
筆者認為《土星》是一個發自內心、充滿熱度、處處善意的作品;那股觸及心靈深處的力量,正是當下都市人需要的滋養:再等一會,總會過的。期待她會成為一個更加精煉和具備追看性的作品,在劇場裡散發溫暖的光芒。
作者簡介
李偉樂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主修編劇(優異)。
憑《塵落無聲》提名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IATC(HK)劇評人獎年度劇本/編劇及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劇本。
近年編劇作品:香港話劇圑讀戲劇場《別來無恙》、文本特區《水中不知流》及「新戲匠」系列《病房》;同流《移家女孩2.0》、《今晚,Omakase夜唔夜?》;劇毒演讀劇《蘇拉超人與索奇星怪的第794回》及三色豆劇團演讀劇場《野戰》(聯合編劇)。
現職編劇和戲劇導師。
《刺客與漁女》:從漁女說起「風箏計劃」三月 公開演讀《刺客與漁女》紀錄文章
「風箏計劃」三月 公開演讀《刺客與漁女》紀錄文章
《刺客與漁女》(以下簡稱《刺》)重新講述春秋時期刺客專諸的故事。對於大多編劇而言,改編歷史故事並不容易。通常觀眾大多已知曉大致情節,甚至能預判角色命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讓當代觀眾重新投入,並賦予故事新的生命力,成為改編歷史劇的最大挑戰。編劇潘惠森曾在《都是龍袍惹的禍》中所言:「時間地點全都交代了,這就是歷史……我最想知道的沒有告訴我。這也是歷史,或叫歷史的秘密。」對筆者而言,改編歷史劇的核心在於掌握講故事的秘訣。歷史的力量在於它所承載的智慧與經驗,但故事能否穿越時空,則取決於講述者如何將它轉化為與觀眾共鳴的情感與哲理。《刺》的創作靈感來自編劇武庭英對專諸故事中魚腸劍的「魚」的追問。歷史的書寫着重在公子光、伍子胥和專諸身上,世人只知「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1],而不見歷史齒輪下的平民百姓、成大事背後的人性掙扎。為了補充這段空白,編劇運用想像力虛構核心角色——漁女姣奴。正是漁女拼命獲得那尾最鮮美的魚,才成就這段流傳千古的歷史。筆者將簡述《刺》的劇本結構,重點梳理「漁女」在整個劇本的作用,以及淺談劇中敍事策略。
虛構角色的作用:漁女的角色設計
《刺》全劇分成六幕:序幕、第一至四幕、尾聲。每一幕圍繞底層市民(代表人物:專諸與姣奴)與權貴階層(代表人物:伍子胥)之間的互動,兩方力量彼此交織,共同推動情節發展。
序幕: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尾聲:
由此可見,漁女姣奴貫穿整個故事。《刺》的主要情節以線性方式展開,從漁夫之死、姣奴慘遭凌辱、姣奴捕魚贖身、姣奴之死,逐步推動主角專諸刺殺王僚的行動,也揭示了底層人物的被動性與無力感。姣奴的犧牲使專諸的刺殺動機變得複雜,同時增添故事的情感張力。
劇中多數角色在歷史軼事中有跡可尋,例如:專諸懼內[2]、專諸母親自盡[3]、專諸之子被封為上卿[4]等。更不用說公子光、伍子胥和專諸,他們在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不僅被大量著墨記載,其背後的動機以及當時的局勢也被剖析得細緻入微。這些資料有助編劇建立每個角色的基調。《刺》的角色形象立體飽滿,有血有肉——專諸的痛苦和舉步維艱、專諸妻子的聰明、專諸母親的智慧、伍子胥的仇恨、公子光的口不對心等。而在筆者看來,姣奴的角色相對扁平,其作用更像是推動專諸的事件觸發點。漁女姣奴敢愛敢恨、不畏強權、勇於發聲,還有她的純潔都賦予全劇更深層次的隱喻意義。或者應該說,漁女更像是高度理想化的象徵。相比之下,刺客專諸的形象則顯得更複雜且豐富,尤其是在與母親交談時的兩段長獨白,深刻揭示了「俠客」與「刺客」的區別以及他內心的掙扎。專諸的行動表面上出於「俠義」,但編劇通過對其心理掙扎的描寫,將他的行動轉化成對命運的抗爭與妥協。他的選擇並非完全出於自由意志,而更像是一種「身不由己」中的「勇氣」抉擇,折射出當代個體的困境。
敘事策略:線性與環形
《刺》的敘事結構結合了線性推進與環形敘事。主要情節以線性方式展開,第一至第四幕描寫了刺殺王僚行動前三天的關鍵事件。如上所述,劇情聚焦姣奴的遭遇,層層遞進的危機推動專諸走向刺殺王僚的高潮。時間的壓縮與情節的遞進成功營造強烈的緊迫感,使專諸的每一步選擇都顯得迫在眉睫,增加追看性,同時突顯出專諸的掙扎與「身不由己」。然而,劇本雖成功塑造專諸複雜立體的形象,對伍子胥與公子光一方的刻畫卻略嫌薄弱,削減了整體敘事的平衡與可信性。劇本有意結合姣奴之死與刺殺王僚的因果關係,並設定王僚要求三天內獻魚,從而限定刺殺行動的準備須在三天內完成。反觀歷史記載,刺殺行動與楚平王之死密切相關:吳王僚趁楚國國喪發兵攻楚,導致吳軍受困,公子光認為時機成熟,遂發動刺殺行動。現時劇本處理雖增加了戲劇張力,卻讓刺殺行動顯得草率魯莽,既低估了公子光的計謀,同時削弱了專諸作為刺客的重量。筆者欣賞編劇通過虛構角色漁女去重寫歷史的宏大敘事,增添個體的聲音,然而如何還原歷史事件中各角色的合理動機是劇本的關鍵所在。
此外,劇本將靈堂設為序幕與尾聲的場景,承載伍子胥與專諸及漁女的鬼魂對話,形成首尾呼應的環形結構。在這樣的編排下,主線的線性推動被包裹在環形結構內,帶來一種凝滯的氛圍。靈堂中的鬼魂對話讓筆者聯想起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雷特》(Hamlet)和邁克爾.弗雷恩(Michael Frayn)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這兩部作品皆改編自歷史背景或傳說,同樣使用鬼魂作為敘事符號。在《哈姆雷特》中,父王鬼魂的出現帶來故事的懸念,促使主角哈姆雷特驗證父親之死的真相並展開復仇行動。鬼魂既是推動劇情的誘因,同時是主角心理狀態的映射。在《哥本哈根》中,三個鬼魂——尼爾斯.波爾、瑪格麗特.波爾以及維爾納.海森堡——共同回顧海森堡於1941年納粹占領下的哥本哈根神秘訪問,試圖從不同視角拼湊出真相。第一幕的台詞「現在,我們三個都已死去……現在,沒有人會再受到傷害,沒有人會再被背叛。」(Now we are all three of us dead and gone...... Now no one can be hurt, now no one can be betrayed.)點出了鬼魂的特殊作用:因為角色已死,他們得以擺脫當時的私欲與偏見,追尋真相的討論因此更為純粹。讀過《刺》後,筆者反覆思索劇中鬼魂的作用可以是甚麼?如果刪去靈堂這兩場戲會影響主題的呈現嗎?在序幕中,筆者一度以為伍子胥、專諸與漁女三者勢均力敵。隨著劇情展開,故事逐漸偏向以專諸的視角推進,姣奴成為推動專諸行動的關鍵角色,而伍子胥則退居為推手與歷史的見證者。筆者思考應該如何理解專諸這位已死的主角?伍子胥在序幕中坦言自己已遺忘眼前這兩個亡魂,專諸才會再次講述那三天的故事。從一人兩鬼的對話帶出主線情節的安排,似乎加深無力感——專諸與漁女是否被困在往事的記憶中,而對世界沒有實質的撼動?為甚麼編劇在序幕要通過伍子胥去引入故事,而不是其他角色,例如專諸的兒子?伍子胥的遺忘是有意抹去他們的存在,還是隨著時間流逝與復仇的快感而無意淡忘?在尾聲中,伍子胥為何能和應亡魂並寄語「能救一個是一個」?這些安排都耐人尋味,值得大家深思。劇本仍在發展階段,但已展現出深刻的思想與編劇刻畫角色的功力,讓筆者期待故事後續發展。
[1] 出自《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2] 出自《越絕書》
[3] 出自《東周列國志》
[4] 出自《史記》
侯亦嵐
現就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戲劇藝術碩士,主修編劇。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中長篇小說入選字花「開故」作家育成計劃。近期編劇作品:呼吸劇團《流離之際III—如廁之夢》及蛇口戲劇節新寫作計劃《蛛絲》。
虛構角色的作用:漁女的角色設計
《刺》全劇分成六幕:序幕、第一至四幕、尾聲。每一幕圍繞底層市民(代表人物:專諸與姣奴)與權貴階層(代表人物:伍子胥)之間的互動,兩方力量彼此交織,共同推動情節發展。
序幕:
- 伍子胥在靈堂上遇見刺客專諸與漁女姣奴的亡魂。
第一幕:
- 漁夫(姣奴之父)因一條魚而得罪權貴,在菜市中被刺死。
- 伍子胥與公子光去菜市場找專諸。
第二幕:
- 專諸在家中與老母親、妻子談論漁夫之死。
- 伍子胥與公子光登門拜訪專諸,從漁夫之死過渡到專諸應該殺吳王僚的動機。
第三幕:
- 專諸在菜市場中得知姣奴被俘虜,更慘遭凌辱。
- 伍子胥出謀獻策,公子光向吳王僚提出捕捉鮮魚的條件,交換姣奴三天的人身自由。
第四幕:
- 姣奴向專諸告白,其後為了捕魚,葬身太湖。
- 專諸帶着鮮魚向伍子胥、公子光覆命,其後成功刺殺王僚。
尾聲:
- 重回序幕的靈堂,伍子胥終於記起專諸與姣奴。
由此可見,漁女姣奴貫穿整個故事。《刺》的主要情節以線性方式展開,從漁夫之死、姣奴慘遭凌辱、姣奴捕魚贖身、姣奴之死,逐步推動主角專諸刺殺王僚的行動,也揭示了底層人物的被動性與無力感。姣奴的犧牲使專諸的刺殺動機變得複雜,同時增添故事的情感張力。
劇中多數角色在歷史軼事中有跡可尋,例如:專諸懼內[2]、專諸母親自盡[3]、專諸之子被封為上卿[4]等。更不用說公子光、伍子胥和專諸,他們在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不僅被大量著墨記載,其背後的動機以及當時的局勢也被剖析得細緻入微。這些資料有助編劇建立每個角色的基調。《刺》的角色形象立體飽滿,有血有肉——專諸的痛苦和舉步維艱、專諸妻子的聰明、專諸母親的智慧、伍子胥的仇恨、公子光的口不對心等。而在筆者看來,姣奴的角色相對扁平,其作用更像是推動專諸的事件觸發點。漁女姣奴敢愛敢恨、不畏強權、勇於發聲,還有她的純潔都賦予全劇更深層次的隱喻意義。或者應該說,漁女更像是高度理想化的象徵。相比之下,刺客專諸的形象則顯得更複雜且豐富,尤其是在與母親交談時的兩段長獨白,深刻揭示了「俠客」與「刺客」的區別以及他內心的掙扎。專諸的行動表面上出於「俠義」,但編劇通過對其心理掙扎的描寫,將他的行動轉化成對命運的抗爭與妥協。他的選擇並非完全出於自由意志,而更像是一種「身不由己」中的「勇氣」抉擇,折射出當代個體的困境。
敘事策略:線性與環形
《刺》的敘事結構結合了線性推進與環形敘事。主要情節以線性方式展開,第一至第四幕描寫了刺殺王僚行動前三天的關鍵事件。如上所述,劇情聚焦姣奴的遭遇,層層遞進的危機推動專諸走向刺殺王僚的高潮。時間的壓縮與情節的遞進成功營造強烈的緊迫感,使專諸的每一步選擇都顯得迫在眉睫,增加追看性,同時突顯出專諸的掙扎與「身不由己」。然而,劇本雖成功塑造專諸複雜立體的形象,對伍子胥與公子光一方的刻畫卻略嫌薄弱,削減了整體敘事的平衡與可信性。劇本有意結合姣奴之死與刺殺王僚的因果關係,並設定王僚要求三天內獻魚,從而限定刺殺行動的準備須在三天內完成。反觀歷史記載,刺殺行動與楚平王之死密切相關:吳王僚趁楚國國喪發兵攻楚,導致吳軍受困,公子光認為時機成熟,遂發動刺殺行動。現時劇本處理雖增加了戲劇張力,卻讓刺殺行動顯得草率魯莽,既低估了公子光的計謀,同時削弱了專諸作為刺客的重量。筆者欣賞編劇通過虛構角色漁女去重寫歷史的宏大敘事,增添個體的聲音,然而如何還原歷史事件中各角色的合理動機是劇本的關鍵所在。
此外,劇本將靈堂設為序幕與尾聲的場景,承載伍子胥與專諸及漁女的鬼魂對話,形成首尾呼應的環形結構。在這樣的編排下,主線的線性推動被包裹在環形結構內,帶來一種凝滯的氛圍。靈堂中的鬼魂對話讓筆者聯想起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雷特》(Hamlet)和邁克爾.弗雷恩(Michael Frayn)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這兩部作品皆改編自歷史背景或傳說,同樣使用鬼魂作為敘事符號。在《哈姆雷特》中,父王鬼魂的出現帶來故事的懸念,促使主角哈姆雷特驗證父親之死的真相並展開復仇行動。鬼魂既是推動劇情的誘因,同時是主角心理狀態的映射。在《哥本哈根》中,三個鬼魂——尼爾斯.波爾、瑪格麗特.波爾以及維爾納.海森堡——共同回顧海森堡於1941年納粹占領下的哥本哈根神秘訪問,試圖從不同視角拼湊出真相。第一幕的台詞「現在,我們三個都已死去……現在,沒有人會再受到傷害,沒有人會再被背叛。」(Now we are all three of us dead and gone...... Now no one can be hurt, now no one can be betrayed.)點出了鬼魂的特殊作用:因為角色已死,他們得以擺脫當時的私欲與偏見,追尋真相的討論因此更為純粹。讀過《刺》後,筆者反覆思索劇中鬼魂的作用可以是甚麼?如果刪去靈堂這兩場戲會影響主題的呈現嗎?在序幕中,筆者一度以為伍子胥、專諸與漁女三者勢均力敵。隨著劇情展開,故事逐漸偏向以專諸的視角推進,姣奴成為推動專諸行動的關鍵角色,而伍子胥則退居為推手與歷史的見證者。筆者思考應該如何理解專諸這位已死的主角?伍子胥在序幕中坦言自己已遺忘眼前這兩個亡魂,專諸才會再次講述那三天的故事。從一人兩鬼的對話帶出主線情節的安排,似乎加深無力感——專諸與漁女是否被困在往事的記憶中,而對世界沒有實質的撼動?為甚麼編劇在序幕要通過伍子胥去引入故事,而不是其他角色,例如專諸的兒子?伍子胥的遺忘是有意抹去他們的存在,還是隨著時間流逝與復仇的快感而無意淡忘?在尾聲中,伍子胥為何能和應亡魂並寄語「能救一個是一個」?這些安排都耐人尋味,值得大家深思。劇本仍在發展階段,但已展現出深刻的思想與編劇刻畫角色的功力,讓筆者期待故事後續發展。
[1] 出自《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2] 出自《越絕書》
[3] 出自《東周列國志》
[4] 出自《史記》
作者簡介
侯亦嵐
現就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戲劇藝術碩士,主修編劇。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中長篇小說入選字花「開故」作家育成計劃。近期編劇作品:呼吸劇團《流離之際III—如廁之夢》及蛇口戲劇節新寫作計劃《蛛絲》。